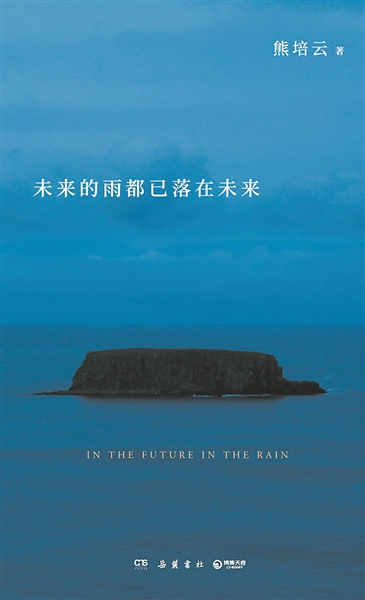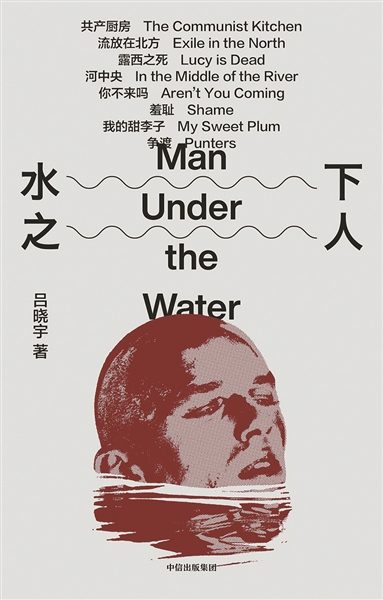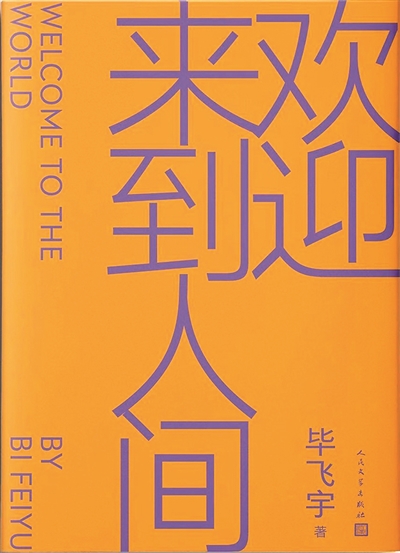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日前,大头马作为“第二届王蒙青年创作计划”的特选作家,在青岛方所书店为她的最新作品集《国王的游戏》做推介,特邀采风中相识的青岛作家艾玛担当提问嘉宾,泛90后写作者在虚拟和现实间跳脱的新异想象,让人到中年、行文深沉内敛的艾玛几多惊喜。年末正值艾玛讲述中年生活和心境的新长篇《观相山》单行本面世,向内寻的静水流深与年轻作者外化的活色生香恰成对照,呈现不同代际书写者观照世界、安顿身心方式与态度的迥异。
2023年,写作者代际之间的“对话”与“碰撞”愈发鲜明。最近一次“理想家”年会上,戴锦华和唐诺两位视阅读和写作为生活重心的前辈,面对年轻一代,也袒露了时下关于阅读与写作的心声。戴锦华坦言,这个世界变得非常陌生,她重新变得一无所知,而她也决定不再试图跨越代沟,因为并不想与代沟那一边的人们一样年轻而成熟,只想保持幼稚和愚蠢,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与他们分享新的思考。
戴锦华会从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发现年轻人不自觉透露出的一种她曾经感觉到却没有用语言讲述的信息,将之视作不同代际人们共同经历的“迷人现场”。这让她充满希望地观看,而不是否决,那些看似重复实则类似文体实验的新的文学形态。
但是这一观点很快就被作家唐诺否定了,这一年他也读了不少网文,其中也有喜欢的,却都集中在前几个章节。他说,他不会夸大重复书写的各种可能。在他看来,文学这个行业毕竟也是一个层级系统,并不是一个平坦的、绝对平等的世界。不是说出自己向往的心事就解决了,文学还需要有记忆,有专业,有长时间的累积。他把这作为文学工作者的一种“老人心态”: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的霍尔顿那样,他想要扮演麦田捕手,要站在悬崖边,小孩总是容易玩疯,要在他们摔下去的时候抓住他们。他所关心的是年轻的书写者能够走到哪里,有了对这个世界错误的期待,到时候会不会沮丧,就像开错了时间的花一样……
前辈的语重心长实则印证了书写日益加剧的代际分离。这一年,我们看到写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年纪所显现的特质与品格,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年纪加入到阅读和写作中间,曾经的书写也在发生改变。而这些基于各自生活、阅读和思维总和的经验投射,最终都成为他(她)们为这个时代所做的注脚,在代际的交迭中留下私属的标记,让时代的样貌愈发清晰。
年纪位移之后改变的事
上了年纪,看到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专职阅读与写作的唐诺在新书《求剑》中给出了答案。书名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刻舟求剑,任岁月流逝,我自岿然于一处,这一处便是那些曾经读过的经典的人与书。唐诺用经验和阅历做出标记,思想的位移随身体的位移自然发生。
因为自身年纪的变化,他在重新阅读经典时发现了一件曾被忽略的事,那就是作家的年龄。比如:莎士比亚,他被叫作莎翁,其实52岁就已离逝,所有伟大作品的创作时间大都在三十几岁的年纪。这让唐诺获得一种阅读的平等感,他在书里看出了“破绽”——那些曾经看不懂的,可能只是当时的莎翁没说清楚,他也会与其他年轻的写作者一样有自己的困惑,不知如何写时也会猜想和跳过。同样被看出破绽的还有张爱玲,当她在小说中表现带着虚无和嘲讽的世故,原来也只是凭借聪明和猜想,而不是真正理解,因为那时的她甚至不到30岁。
曾经让唐诺感到无比熟悉的阅读,因此好像有了再重读一次的必要。这成为写作《求剑》的缘起:“这本书好像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可以逐步去理解年纪、老年是怎么回事。而老年在文学史上通常是被忽略的,因为只有老年人有这样的经验,但是60岁以上的经验只有活到六七十岁以上的人才有。即使文学这么浩瀚,也没有真正被巨细靡遗的穷尽,我想去理解这个过程。”
在唐诺看来,一个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多样,呈现在作家身上则可能是不被理解的失败。他不止一次提及托尔斯泰和海明威,前者公认的最失败的作品,是他最后写下的《复活》,“曾经技艺高超的狐狸型的人,最后却写了这样一本看起来沉闷的,连文字都变得笨拙的小说”;后者的《渡河入林》,在文学史上同样被认为是海明威最失手的作品,擅长叙事的他,在这部作品里“连对话都写得一塌糊涂,肉麻,真的难受”。
不过,上了年纪的唐诺现在越来越认同马尔克斯对于《渡河入林》的评述:这虽是海明威最失败的作品,却也是他最美丽的作品。在与梁文道的一次对谈中,唐诺再度谈及这部小说:“他写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并且意外地成为他自身命运的寓言。我觉得是一直抗拒年老、调笑死亡、自认为英勇的海明威,第一次无隐地碰到了年老跟死亡这件事,他不知所措,所以反而很真诚地写下它,包括他说不清楚的东西。里面藏有非常多的讯息,甚至比他成功的作品会看到更多真相。”
唐诺鼓励年轻人去看作家们失败的作品,包括他曾经评判过的米兰·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那部小说“几乎跑了我们认为难以忍受的粗俗的东西出来”,他认为最恰当的方法是,留一个不舒服的异议的声音在心里。也许到了某个年纪,某一天某个状态之下,会从中看到不同:“有些部分可能是衰败、入魔,或是某种落幕,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所在意、强调、凝视的究竟是什么。而你愿意坐下来体会。”
苍凉感知中的现实之问
即将进入耳顺之年的作家毕飞宇,2023年推出新长篇《欢迎来到人间》,这部医疗题材小说,据说创作过程极其艰难,前后写了一百多万字,最终却只呈现了20万字。《收获》主编程永新评价它,并没有很强的故事性,而是通过建构精神世界,刻画典型人物当下的精神状态,令人惊叹。
故事发生在“非典”时期的一家医院,泌尿外科肾移植接连出现六例死亡,通过傅睿与他身边的一群人——医生、患者、护士、老院长、“贤妻”的视角,毕飞宇不断发出拷问:时代和城市究竟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小说中发出振聋发聩的现实之问,这是毕飞宇一贯的风格,《推拿》是结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平原》亦然,而到了《欢迎来到人间》却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特质。
在此前的媒体采访中,毕飞宇坦言,他一点一点地感觉到了生活的苍白,甚至于苍凉,这种感觉年轻时候不太多。“不过苍凉也好,苍白也罢,都是老天爷给予人类的感受力。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你必须张开你的手臂,把它接住,从生到死一个漫长的年龄阶段,每个阶段你都要有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清静也好,疏离也好,可信也好,不可信也好,最后你得告诉自己‘我是这样的’。”
或许正是源于内心的苍凉感,他打破了写作的惯性,“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小说叙事风格,一套小说美学,这是我的幸运。按道理来讲,在作为一个作家的黄金岁月里,我可以沿着以前的轨迹慢慢走,问题是,我建立得太早了,我要面对一个选择,是沿着我已经建立起来的语言风格往下走,还是要重新做人?我决定重新做人、重新做一个作家……”
毕飞宇相信,《欢迎来到人间》即使不足以涵盖当代,但其中的精神历程,是我们都曾经面对的。他说:“我只关心当读者看完小说之后,能不能感受到我的情绪;如果读者能从小说里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撞击,晕头转向的,哪怕不一定读懂小说讲了什么,这部作品也就成功了。”
同样感受到内心苍凉的还有一位在2023年“复出”的作家熊培云,他的诗集《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在年末出版,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前半生的世界是蒸蒸日上,后半生的世界是摇摇欲坠。这种对比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的肉身。人到中年,身体每况愈下几乎是必然的。很多时候疾病不只是疾病本身,疾病还是一味药,它能医治许多关于人生的毫无意义的幻觉,比如来日方长。回想我曾经写过的书,其中大部分都是希望国家与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朝着自己期许的方面走,然而作为一介书生,这种努力多么微不足道……
在完成“从众心之心到众我之我”的转变中,这位人到中年回归诗歌创作70后写作者这样表示:“世界固然大到无边,但在我看来领略人生之无穷远比世界之无穷更有意义与价值。这世上有一种可能的悲剧是,我们走了很远的地方,却没有走进自己的人生,那些原本是我们最想要去的心底的花园从未涉足。”
以肉身投入世界的真切
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给了90后作家杨知寒的小说集《一团坚冰》。书名即传递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坚硬、冰冷、力量感。她在2023年推出的小说集《黄昏后》,则是这一冷硬风的延续。
杨知寒的故事中,从《一团坚冰》里隐身佛寺的辍学少女、苦等搭档的落魄民间演艺者、送走老虎的驯兽师到《黄昏后》里不被理解爱人,“我”与师妹相爱的悲情结局,退休女司机孤独的黄昏恋……她写人与人之间的幽暗晦涩、爱与恨的关系,闭塞的环境、寒冷的气候、乏味的日常生活与绝望中人的命运融为一体,而这严寒中却总留一点微光……
在这位网络文学转场“纯文学”的90后小说家身上,你会发现当下年轻书写者具有的某种共性,他们有不拘泥于题材抑或表现形式的勇气,总是热切地传递个体的生活经验与感悟,他们以肉身投入世界的方式真切而生动。
另一位95后作家讲述的故事,则来自一位中年母亲的视角,围绕这位母亲追寻女儿留下的谜团的真相,在亦真亦幻的氛围中展开叙事,神秘的童年好友、二十年未见又突然出现的恋人,在时空的回溯中重逢,诉说两代人的隔阂与谅解。出生于山东聊城的武桐,以剧本写作为业,《火车驶向落日》则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2·夏卷》,让他成为首位由《收获》推向读者的95后青年作家,可谓“出道即巅峰”。
小说结尾,火车终于开进了落日,过往的错误在那一瞬间得到承认和释怀,失去的一切,也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这是年轻人的生活理想,他们总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困惑,安顿自身。
同为90后的王苏辛在个人小说集《再见,星群》里选择以另一种方式为自己释惑。《猎鹰》中的母鹰和小鹰,有一天小鹰从空中往下掉,母亲开始是常规地担心,然后要冲下去呵护它,飞到半途,发现小鹰“也像在证明什么似的……换着姿势在半空中挣扎着奔跑”,所以母亲又带着信任和骄傲开始飞开一定的距离……这是有关成长的讲述;《远大前程》里的男孩儿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一幕场景,是对孤独的描摹,王苏辛总会在小说的细节中处理一些看似宏大的命题,而这两者对她而言是统一的,即:如何在孤独中面对自己,获得成长。
相对于同龄的写作者,王苏辛的小说似乎过于理性了,她并不注重人间烟火中人物的塑造,更倾向于用细节来说理,探寻问题。在《灰色云龙》里,她探讨年轻一代走入社会的人生,认真把同代人思考的问题放置在小说里;在《寂静的春天》里,她借想成为艺术家却做了医生的女主人公之口,提出自己的观点:“艺术的基础其实不是感性,而是理性”。在《绿洲》里,拾荒者黎姐结识了一位白领,有一天打电话问对方能否去她家小住。故事并没有走向住在一起后的戏剧冲突,黎姐带着自己的帐篷,只是住在了她家附近,唯一更亲密的可能是会把手机放在对方家充电……“帐篷”即对应了小说的标题“绿洲”,这个情节让评论者感到了精彩,那是一种精神性的溯求,来自以肉身投入世界的年轻的书写者真切的精神探求。
虚构与真实交织的时代返照
2023年,当我们翘首世界文坛时发现,2022年出版的一本来自80后智利写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小说《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获得了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国际文学奖。这一对国人而言有些陌生、却是时下最重要的世界文学奖项之一,让这本书隔年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讲述了五则天才科学家的故事,重点在于,这些科学家的名号尽人皆知,而有关他们的故事却纯属虚构。拉巴图特把握住了时代性,用虚构和真实交织的文字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狂热和绝望。
将虚构与真实交织杂糅,这也是中国当代写作者中盛行的一种尝试。吕晓宇的《水下之人》面世时,口述、访谈、新闻报道、独白、时事评论、诗歌等语体复合的复调结构,着实惊艳,这个发生在2069年的故事以“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无意发现的中国青年L的手记为引,勾勒L的一生……有关这个无名者的“消失”和“进入”的始末,在虚构的历史维度上,展开的是21世纪世界青年一代的集体境况,个体与现实、历史的对峙,才是作家吕晓宇书写的意图。而杂糅的文学形态,似乎最大程度地迫近了混乱时代缝隙中的“水下之人”的境遇。
从2022年的旅行游记《东游西荡》到2023年的小说集《国王的游戏》,生于1989年的书写者大头马也在做着虚拟与现实相互缠绕的文体实验。今天,游戏世界或者虚拟世界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大头马的敏锐在于精微把握了时代里每个人虚拟与现实犬牙交错的生存。一直关注青年女性创作的评论家张莉,不久前在讨论“女性文学好书榜”秋季书单时发现,游戏,已成为年轻写作者喜闻乐见的小说题材,而如何将现实丰厚的复杂性在虚构的历史与情节中得以更成熟的呈现,如何在照应生活的尝试中给予读者更深切的情感共鸣,也成为一代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新挑战。而大头马给予青年同道的启发则是,她从奇崛处入手,使我们得以用另一种方式重新返照现实。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