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君
小区院子里,我居住的楼座西南侧有两棵树。我几乎每天都会在阳台看一会儿这两棵槐树。我觉得它们一定是从同一个村庄或者同一片山林移植来的,像孪生兄弟或姐妹般,在这陌生而喧闹的环境里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节奏成长着,树冠几乎一样高,主干几乎一样粗,各自的大部分枝杈朝着同一个方向伸长。我草率地认为这两棵槐树是在眺望故乡,因为它们更多的枝子没有往阳光直照的方向长,而是另一个共同的指向。这两棵槐树距离很近,树枝却很少搭连,更多的力气都用在往高里蹿长,好像是为了尽早望到家乡那片天空。所以我觉得它们是孤独的。
大概五年前,一对喜鹊从天而降,消解了这两棵槐树的某些寂寥,使它们显现出了庇佑众生的善本意。那两只喜鹊绕着这两棵槐树起起落落,选定了一个三分枝树杈开始垒巢。那些日子里,看着它们从日出忙到日落,我脑海里无数次浮现出在老家盖房子时帮工的乡亲们扛抬檩子椽子的身影,浮现出城市建筑工地上搬运钢筋和水泥构件的农民工的身影。农民工在城里是给别人盖房子,乡亲们是义务帮忙给我家盖房子,喜鹊是给自己盖房子。
接下来的这几年里,那对喜鹊夫妻每年都在它们的巢里养育儿女。像所有的父母一样,从早到晚四处觅食,带着羽翼未丰的子女熟悉外面世界,悉心传授生存本领,最终把它们送走。一年又一年。站在阳台注视喜鹊和它们的家,感觉好些莫须有的寂寥与浮烦也飘散而去。我因此对那两棵槐树心有感激,它们让一家子喜鹊安居乐生,带给我只有我自己心领神会的慰藉。而槐树似乎也更蓬勃,更快意,它们的主干更加坚挺,枝杈更加舒张,叶子更加茂密。
然而,就在这个冬天,预示“鹊始巢”的小寒一候里,离开了一段时间的喜鹊回来了,而且不只是两只,是四只大喜鹊。我一阵窃喜,以为原来的喜鹊请来一家邻居,要加盖新巢,开始又一年的幸福生活了。可是,它们并没有出去衔运树枝,只是在树上跳来跳去,围着原有的巢逡巡审视。它们的叽喳声像是四个人在低沉而严肃地讨论问题。我当然听不懂,不知道槐树是否听明白了它们说的什么。
几天之后,这四只喜鹊拆掉了原来的巢。它们飞去又飞来,飞来又飞去,将垒砌旧居的树枝一根一根地衔走。我不知道这些建筑材料被送往了何处,只是想喜鹊们可能悟到了某种玄机,寻到了更适宜的安身乐命之处。那鹊巢一天天被拆散,只剩下最底层的几根枝条别在槐树的杈丫上,像留存的一处老“地基”,枯然地寂寥着。喜鹊们不再回来了,院子里一下子显得空旷了许多,听不到它们响亮浑厚的会话和歌声,只剩下麻雀、乌鸫、白头翁们偶尔的“叽叽”“啾啾”,很有些沉闷了。而我的失望和落寞也一缕一缕地,从阳台的窗口飘弋出去,飘到了槐树的枝头,垂挂成似有还无的黄叶。而那两棵槐树好像也失去了热闹的气息,在冬末的风中瑟缩着,光秃又迷蒙的枝梢很有些茫茫然地摇曳在虚虚的半空里,再度孤独起来。
单从名字看,喜鹊就应该是一种特殊的鸟,小到麻雀大到孔雀的鸟都叫“雀”,唯独它单占了一个“鹊”字,不知道人们当初造这个字命名这种鸟的初衷是什么。我只知道这种性情机警的鸟是很有人类缘的,它们喜欢在人的居所周围筑巢生活,繁衍后代,中国人对它的名字前置一个“喜”字,认它是吉祥的象征。而那两棵槐树,在我老家叫“家槐”,还有许多地方称之为“国槐”,人们愿意在房前屋后栽植它们,还赋予它迁民怀古的寄托与平安祥瑞的意韵。如此看来,喜鹊选择在槐树上筑巢造屋,对于二者都可谓最理想的组合,犹如梧桐凤凰、骏马锦辔。我相信搬迁走了的那几只喜鹊,一定是迁到了另一处槐树上筑就了舒适的巢窝,开始孕育它们的又一群儿女了。但它们的老巢“地基”还在,还在原来的槐树上,像一只眯起的眼睛,张望着喜鹊飞去的方向。明年,后年,或再过几年,搬走了的喜鹊或它们的子女,会不会怀念起老宅,重新回来,在老宅上兴建新宅呢?
我宁肯相信会的,我盼望着。槐树也会盼望的,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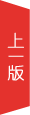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