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启昌
海边人常说,小海货里也有大乾坤。
小海货的烹饪方法多是蒸或煮,要不就是油炸、油煎。它们个头儿虽小,但天生具有的鲜美滋味让其自带了同样能登大席面的资本。还有一种使小海货身价倍增的加工方法,让尝过其味的食客无不咂舌称好:制酱。小海货蝶变而成的酱种类不少,像虾酱、蟹酱、比管酱、鱼杂儿酱等等,都是海边人一年四季饭桌上常见的抿酒下饭的海味佳肴。
我也枕海而居,自认对大海鲜、小海货格外熟悉,吃的比旁人见的都多。每有此类话题,往往会凑上前去叨叨上一阵子。今夏去烟台,在靠海的美食街上尝到了一道深度唤起我馋意的海味好菜,竟让我在海鲜美食上“见多识广”的优越感黯然失色了若干。
这道好菜的成本极低,可谓是“废物利用”的成果。“海怪酱”!我乍听到这个菜名甚感奇怪。尽管朋友再三褒奖“海怪酱”多么有营养,味道多么独一无二,我还是好大会儿未能下箸。搞不懂它的来路,把不准它为何有这么个怪吓人的名字!朋友郑重介绍,“海怪酱”得来不易,是专用寄居蟹剁碎磨细、加盐发酵制成的。因寄居蟹并非量产,是渔业副产品。渔民珍惜大海的馈赠,择取寄居蟹可供食用的肉脂膏部分制成酱品,以悦味蕾,以饱口福。
探清“海怪酱”底细,我和同行朋友纷纷执箸尝鲜。果然,这“海怪酱”与鸡蛋配伍,在葱碎儿、姜丝和小米辣的帮衬中,借助热油撮合而生成的菜肴香且鲜,入口嫩滑,蟹肉之味突出,没有蟹壳细渣,回味悠长。朋友介绍,“海怪酱”就饭,米饭也好,面条、馒头也罢,各取一匙即可。我爱吃面条,挖一满匙“海怪酱”入碗,与紫菜蛋花浇头一起“调合滋润”面条,浓香气息扑面,令我食欲顿生。紧临而座的女士将一匙“海怪酱”与米饭相伴,执箸搅拌,原本白花花的大米饭少顷成了金褐色。好看的色泽,好闻的味道,让第一次吃到“海怪酱”的她越发喜形于色了。对坐的两位伙伴,掰开白馒头,各自将满满一匙“海怪酱”耐心地塞了进去,继而又沿馒头边捏了两圈儿才入口咬了。咀嚼间,两位觉得麦香跟“海怪酱”的香鲜融合,其沁人之味和悦动味蕾的指数,均可与声名颇大的“肉夹馍”一比。
吃过“海怪酱”,我忆起小时候的一些过往。当年所在的小村子,几乎家家天井里都安有一盘水磨。除了磨豆浆馇小豆腐,水磨的另一个用途便是将海上捕捞的小虾小鱼等研磨成稠浆状,继而装进瓷坛里加盐调好,密实扎紧坛口,搁到阳光照到的地方等待发酵海味酱吃。那时,日子过得普遍拮据,不过,过惯苦日子的村人们因为一口海味酱的滋润,脸上倒也不失暖意。我记得,我家天井中的水磨还常磨过“嘟噜蟹酱”。父亲在外行医,有了薪水,会去镇上集市花块把钱淘半兜子嘟噜蟹,拎回家让母亲磨了做“嘟噜蟹酱”,给一家老小乏味的饭碗里添几分化解馋念的美味。嘟噜蟹多在泥质滩涂栖居,肉少壳厚个头小,用其制成的酱味道差劲,跟“海怪酱”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日子渐好后,老家人做“嘟噜蟹酱”就变成了记忆。
吃“海怪酱”还让我想起一件事。青岛城阳沿海一带有道如今仍在溢香的好菜:鱼杂儿。鱼杂儿也可称作“鱼杂儿酱”。渔民出海,随机加工渔获时,不舍得丢弃“鱼下水”,集中到船上备好的大桶内加盐腌制。日子一长,“鱼下水”在发酵中演变成黏稠的酱状。将“鱼杂儿酱”盛碗清蒸蘸葱吃,或淋入小磨香油炖熟就馒头、浇米饭,或是“鱼杂儿酱”里磕鲜蛋炒着吃,那鲜那香总能叫人胃口大开,饭量陡增。
物阜民丰时,用好食材烹制好菜肴很容易,享口福并非什么难事儿。同样情境下,若用不起眼的“糙物”,或者本可列进废弃清单的“次毛”食材烹制出美食来,除了上乘的技艺,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就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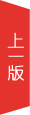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