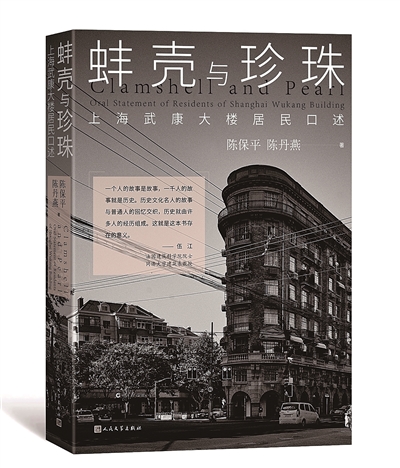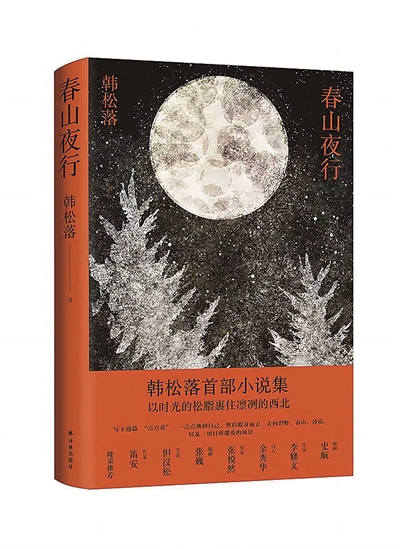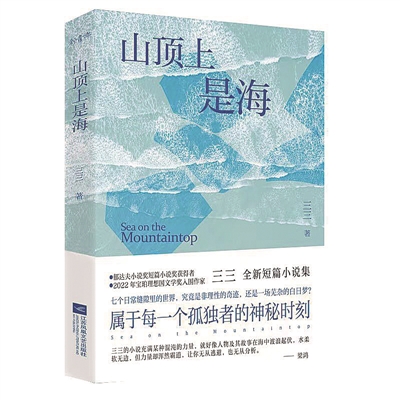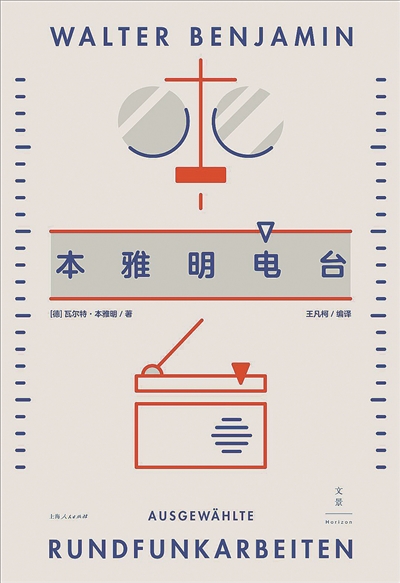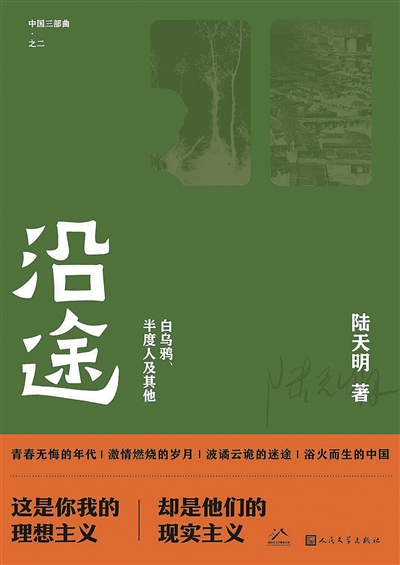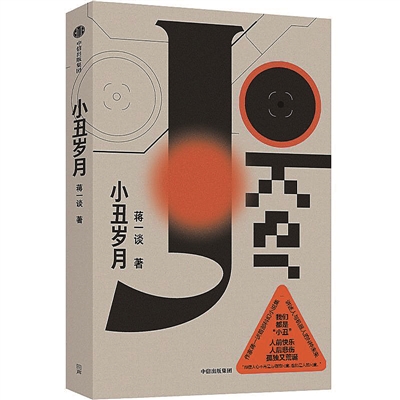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记者在上海书展的旅程以瓦尔特·本雅明的“电台广播”作为开端。位于历史风貌保护街区的思南文学之家,一个文学的夜晚,本雅明作为初代播客,在新书《本雅明电台》中“发声”,以其与生俱来的表达天赋,于其不安定的生活中尝试迎接一种新兴媒介时代的到来。
今天,技术定义并掌控着每一个人,使之陷入精神的匮乏。在本雅明所在的近百年前的时代,勇于接受技术与新知的他对此早有预感,也因此更加执着于回到讲“故事”的传统。本雅明所谓的“故事”源于一些拥有相同特征和相似生活的人,是一群人在共同生活中,彼此交流各自经验的产物。“故事”唤醒我们内心的体验,让我们告别贫乏,回归真实丰沛的自我。
与本雅明一样,上海书展上那些在书的精舍间漫游的语言文字,也在接续传统,讲述新的“故事”。于是,在经典译作中,我们发现文学的原乡与方向;在索南才让的《找信号》和韩松落的《春山夜行》那里,我们获得了关于西部叙事的风格迥异的生命体验,从草原到西部小城,或奔放,或细腻,听他们以切实的经验“怀旧”,谈论生活、死亡、时间、命运;在作家三三《山顶上是海》中编织的七个不同故事里,我们看见不可能之事成真,感受习以为常的世界中陌生奇异的质地;在陆天明和他的新长篇《沿途》中,我们重返知青历史现场,体验新中国初代、二代人们的命运和生活;在蒋一谈《小丑岁月》构建的人与机器的未来伦理中,感知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温情……
当作家阿来在书展上提及文学的功用——“感知世界”,我们知道,对于“故事”的热爱与推崇必将拓展我们对于世界的共有感知,为精神生活做出辩护。
在经典译本中理解文学的过去与未来
上海书展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在驻地上海世纪出版园举行了第二届“译文双年选”的颁奖礼,当天持续的雷雨天气似乎也在见证经典译本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评审团最终将奖项授予了郑体武翻译的《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和刘象愚翻译的《尤利西斯》。
经典译本引出关于翻译文学以及文学发展的回溯与思考。简短的沙龙活动中,生于60年代的毕飞宇谈及经典译文对于同时代中国写作者的重要意义:“作为汉语写作者,如果没有大量翻译文学的阅读与学习,想要成为一个小说家,是不可想象的。”他坦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自己投身写作的前五六年甚至七八年间,所选择的语言风格依然是翻译体,有意无意间,行文会向译本语言靠拢。因为“对于不自信的年轻写作者,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告诉自己‘我在写小说’。从我个人的写作传统来讲,翻译文学是决定性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我的写作不成立。”而作为一名热爱诗歌的作家,毕飞宇也明确了诗歌阅读与他的小说的关系:“如果你认真阅读我的小说,那么一目了然——这个写小说的人一定是读诗的,诗在我的小说里至今有痕迹。我当然知道不能用诗歌的语言去替代小说叙事,但是对诗意的痴迷,不可置疑。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不读诗,那叫什么热爱文学?那就是一个谎言!没有能力对诗歌进行审美接收的人,如何能去写小说?起码他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今天的文学水准是否大不如前,或者说整个世界的文学门槛都在下降?对于这一追问,作为评审团主席的李敬泽持绝对的宽容态度。他说:“我相信每个时代都会确认和发明自己的文学性。从文学史的发展看,我们现在认为的文学,倒退一百多年,也许并不被看作是文学。因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文学,其实就是译文所捍卫的充分经典化、秩序化的文学,有来路、有去处,而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感知世界感知自我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大变化,由此一定会带来对于叙事、想象、情感表达方式的挑战。”在他看来,经典的传统形式,可能有朝一日会变得面目全非。“我确实不能理解怎么能够15分钟甚至5分钟就能讲完《红楼梦》,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包含着新的秩序结构,许多人就是需要这样的方式,当然现在这种方式可能是粗糙的,但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时代或下个时代中一定会有绝顶聪明的人,把当下散乱的、没有充分自觉的讲故事的方式,锤炼成为对一个时代有利的,甚至经典型的未来艺术形制。”
在热门的“西部故事”中感知生活的他者
位于上海的网红文艺地标安福路上的塞万提斯图书馆,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与来自兰州的作家韩松落带领读者进入《找信号》和《春山夜行》讲述的“西部故事”中——
《春山夜行》是一本带着九十年代气息的、“私小说”式的小说集。这本书创作时间跨越30年,从带有一定自传色彩的《妈妈的语文史》到韩松落打捞记忆写出的“农场故事”“世情”系列,带着些许传奇色彩,为在时光中远去的边缘人立传,也留下了他曾经生活的西北世界的风土人情、自然地理、方言土语以及隐匿其间的粗粝与温暖。
《找信号》则是来自青海的第一位鲁奖得主索南才让获奖后的首部小说集,呈现“最后一代游牧人”眼中草原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危机。那些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怀疑、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的茫然无措者,是身为牧民作家的索南才让小说的焦点。
韩松落从对索南才让小说中死亡方式的统计出发,赋予他的小说不同维度、更深层次的意义。他发现,索南才让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种“前现代”的死亡方式,死于大自然、死于风暴、死于与动物的冲撞抗衡……而这种写作方式在诺奖得主艾丽斯·门罗的小说集《逃离》中也有显现,凡是逃离小镇的人都死于一种现代的方式,比如飞机失事、车祸,或者一种城市疾病,但留在小镇的人都会死于溺水、海难或者是被动物咬死……门罗用这种死亡方式区分鲜明的人物处境:现代的或是先现代的。
而在一个人们的内心都被数据化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观察、应对“先现代”的生死,比如面对气候的灾变。而当下写作的意义正在于此——让我们回到“先现代”的现场,重新处理人与自然、与土地、与身体、与死亡的关系。在韩松落看来,现在的小说更多处理的是人与物质以及人与一个虚拟的系统之间的关系。他将索南才让的小说纳入安妮普鲁式的生态小说,并特别提到他在那篇极短的《黎明》的故事中,让几代先辈的身影在夜晚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袭来的场景,他认为,那也是一种动人的对心灵生态的修复。
刚刚凭借《雪山大地》投票第一的成绩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青岛作家杨志军,也在位于上海展览中心的上海书展主会场现身。尽管定居青岛26年,但杨志军每年都会回到西部,回到青海,回到草原牧区,延续个人的情感与创作,他称之为生命的延续。《雪山大地》将人们带入作家的父辈以及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西部探索足迹,展现藏族游牧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他说,过去自己的高原写作,也许更多关注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而现在的书写所关注的,更多则是当下的生活。在他看来,作家理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必须唤醒他所熟悉的那块土地。《雪山大地》中的人们正在告别他们所熟悉的游牧民生活,他希望这种告别以及告别之后的新生活,都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摆放于作家出版社展台醒目位置的《雪山大地》,成为书展上媲美广西师大出版社网红卡夫卡书袋的超人气畅销书。而真正令作家欣慰的,则是读者对于文字的高度感知力。几天前,书的编辑姬小琴贴出了一名读者关于这部小说的阅读体验:这是一种彻底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另一种高密度的日常生活。可以给平庸的日常平添许多乐趣,甚至可以在内心里滋养出一个精神的原乡。它让我确信,人的生活,确实是可以有另一套表达系统的,也可以全频道充满诗意。这应该是本诗集,但它又确实是本小说,还原了生活的原色。”
在对日常的颠覆中探寻智识与自我
出现在上海展览中心书展主会场的三三,因为她新书奇异的书名《山顶上是海》而倍受注目。这本书中的七个故事,描述了七种隐秘而决绝的生活:有婚姻关系充满隐疾的夫妻,消失多年、从事“羽人”工作的故人,葬礼前后形迹可疑的亲人,在情欲和道德中挣扎的青年男女,将“猎龙”作为人生理想的年轻男孩,背负旧日伤口的校园恋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真实生活的受难者。
而在《羽人》《暗室》《猎龙》《仇雠剑》等一众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名称中,三三选中了《山顶上是海》作为书名,这个短句给人一种时间地理的错乱感。缘于一次《喜剧之王》拍摄地石澳岛的旅行:远道而来的猛浪在礁石上拍碎,化作白沫,如同一片海出现在山顶——这个场景似乎成了一种关于精神空间的象征,写作者的敏锐让她感知其中的意味:这是不可能之事的成真,是对以往生活细节的超越,是对人生中诸多虚无劲敌的反驳。
那天的活动现场,作家索南才让作为嘉宾列席,他说三三的小说让他想起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擅长编织怪异、黑暗、暧昧的恐怖童话故事,细腻、奇异。《山顶上是海》是三三写作生涯的第三本书,此前她已出版了长篇小说《离魂记》,短篇小说集《俄罗斯套娃》,以及今年刚刚面世的《晚春》。她的写作表现出一种远超同龄人的冷静和锐利,包含了对悬疑元素的机巧把握,被余华称为“有把恐怖小说变成高级文学的天赋”。
三三认为,写作者要书写的并非现实,而是人的精神层面。生活中一定存在奇迹,而这个奇迹很可能发生在人的精神层面,超越工作、通勤、人际关系和所有琐碎的日常。“对我来说,写作一个探取智识、探寻自我的方式。”
与三三一样在写作中探寻与反思现实的还有蒋一谈。在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一个与鲁迅有着深度关联的文学场域,转型科幻写作的蒋一谈和他的科幻小说集《小丑岁月》亮相。此前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鲁迅的胡子》曾经寓言式地呈现一位神似鲁迅的捏脚师傅孤独纠结的自我。
而“跨界”科幻题材,蒋一谈并没有丧失对当下生活的敏锐把握。在未来图景中,他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重构,而他所描摹的独居老人,以及他们与机器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也超越了庸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温情动人。在作为新书分享会嘉宾的学者周立民看来,蒋一谈对于人和人的境遇的关注,包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在小说中一直延续。他不断拓展他的题材领域,同时又始终抓住文学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即对于人的命运和自我的叩问。而这些问题始终具有被思考的意义,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恒定的价值。
在老故事中反思当下的人生意义与价值
暌违六年,80岁高龄的作家陆天明“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沿途》出版,上海书展期间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的附属建筑友谊会堂。小说中,有志青年们走出西北荒原、莽莽农场,人生地图徐徐展开。
关于第一部《幸存者》与《沿途》之间的关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提出,《幸存者》是青春的书写,而《沿途》是盛年的书写,前面是走出去的写作,后面是回归的写作。人生到了80岁,其实到了要总结自己的来路,或者说这一代人的来路和命运的时候。林语堂有80自述,王蒙有80自述,这部陆天明的《沿途》也可以看成是他的80自述。作家陆天明出生于1943年,上世纪60年代初到了边地、到了新疆、到了兵团,这一代人对命运的总结梳理与回溯,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在第二部《沿途》中,陆天明用电影闪回的镜头把故事场景代入到第一部《幸存者》的时代,重返知青历史现场,重新书写新中国最早的两代人的命运和生活。他还在新书分享会现场讨论了书中“理想主义”的问题。认为,没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是虚空的,会遮蔽我们对于现实的关照;反过来讲,如果现实没有理想的指引,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全能主义者,找不到真正的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他和他的时代因命运使然,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和命运,而现在中国人的命运仍在“沿途”中。
何向阳更进一步讨论了有关“知青文学”的问题。在她看来,知青一代的故事在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都在不断延续,他们的思索、他们对自己和家国的“反刍”仍在继续。从这一层面来看,知青文学其实是没有终结的。而谈论知青文学,不能只停留在理想主义、初心和信仰的状态,应该从他们的人格建构、成长状态去理解。小说《沿途》中提出了“半度人”的概念,即一脚踩在现实的土壤,一脚留在理想的空间,处于矛盾、撕裂、挣扎的状态。在对自己进行自我探索梳理的阶段,陆天明是要通过《沿途》了解他自己、了解一代人。
这又让我们想起作家韩松落的话,在回答作家为什么都热衷于书写过去的老故事的问题时,他说:怀旧看起来是从过去搬运东西到现在,实际上是从现在搬运东西到过去。是用我们的新进展、新理论、新心得,去发现过去、理解过去。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