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启昌
年底,连刮整天的西北风终于在傍晚掌灯时消停下来。不过,天没放晴,云低沉着,像是要落雪。
果然,雪悄无声息地洒了一夜,村子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西屋杨叔大早敞门,执一柄新扎的竹扫帚一路清扫到我家门口:大侄子,雪住了,我打好糨子,帮着贴年红哩!
过晌,院落里外贴好的年红与晃眼的白雪互映着格外好看,杨叔望着这番景光心里恣得不行……
四十年前腊月根儿上的这一幕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年,我还是读初中的学生。如今,我已两鬓染霜,而杨叔只留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里了。
贴年红是庄户人家年底非忙不可的营生。杨叔跟别人一样,对此看得很重。早年,还没进腊月,杨叔踫到我就说:“侄子,等年根儿上,还得帮我贴年红。”每每我都点头答应。见我点头后,杨叔总爱掏出烟袋摁满烟面子点火猛吸,香喷喷、辣乎乎的烟雾飘开时,他笑着夸我贴年红仔细,贴得格外好看。还说,年年正月来家里串门的亲戚、邻居看了都夸好。
杨叔家家口多,房子比我家多两间,院落里还有羊栏、猪圈、兔舍、鸡棚、烤烟房,还挨排着安有四口水泥粮缸、两个又粗又高的粮食囤子,西院墙外还有两间牛棚。年红包括的东西多,除了门对,还有福贴、炕头贴、棚圈贴、年画、窗花啥的,一揽子贴板正了,得花一两个钟点。不过,我每年帮杨叔贴年红都很用心,该贴的地方都贴,哪个地方该贴啥就贴啥,要不,杨叔怎么老夸我呢!
我贴年红时,杨叔当帮手。他老早在锅里打好糨子,再舀到瓷盆里,在哪里刷糨子,刷多少糨子,他拿着锃新的饭帚听我调遣。等我贴上对应的年红后,杨叔用全新的笤帚将年红自上而下、自左而右扫平,压实。每回贴好一处,他都后退几步细端详,继而竖起大拇指说:“好!很端正,挺好看。”
我当兵那年离家走的时候是冬月底,心里光激动了,忘了年底杨叔家贴年红的事。军营周边响起零星的炮仗响声时才记起来,遂给父亲写信,让父亲抽空帮杨叔忙活贴年红营生。父亲在外行医,是有心人,回信说,年根儿肯定帮他办得妥妥帖帖。
从部队退役后,我进城当了工人。不久,便和父母一起搬进城里住了。工作、生活节奏一年比一年快。不过,再怎么快,我都没搁下杨叔家贴年红的事。临近除夕,骑脚踏车,后来改开车,往返六十多里地专程回老家操持杨叔家贴年红营生。
杨叔很爱“好”,他不喜欢书店里卖的统一印制的年红,说集市摊子上现写的好。每年嘱咐我买的时候都这么说,而我也是听他的话专门抽工夫赶集帮他挑。买回后,再说给他听,给他解释年红的定义,以及年红中所包含的寓意。听了,就夸我上学多,知道事多,买的年红准差不了。
杨叔刚过九十岁走的,是个腊月天,风大格外冷,他家大门口挂的纸幡锃新,而贴在两扇门还有门框、门楣上的年红却早已褪净了颜色。我去付人情时,跨步门槛,心里陡然生出阵阵酸楚。
光阴荏苒,时光不再。如今过年我依然愿意回老家走走,其中一件事是给杨叔故居尚矗立着的院落大门贴年红。
杨叔一辈子勤劳,可是没念过书,杨婶也一样只字不识。两人因是近亲,子女虽进过校门,但也只是进过校门而已,年红上的字义都解不了。不幸接踵而至,杨叔过了耄耋之年后,家里人或因病、或因意外相继离他而去了。杨叔家的老宅子除门楼及门楼下的两扇大门矗立着,正屋,还有羊栏、猪圈、烤烟房早都墙倒顶塌,现今,空留一处屋框子在继续经受着岁月的蹂躏了。
回眸过往,我多么希望这个年根儿上,能再有机会在白雪映衬下,给杨叔家再贴一次年红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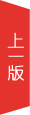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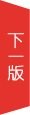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