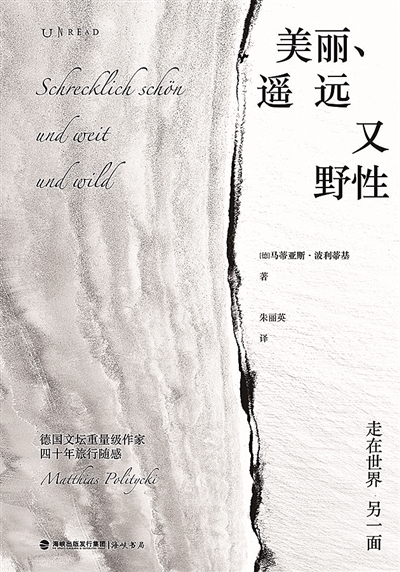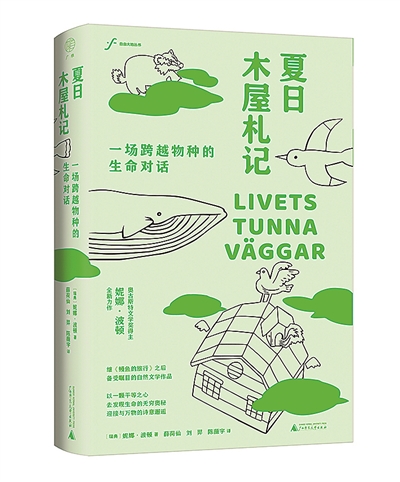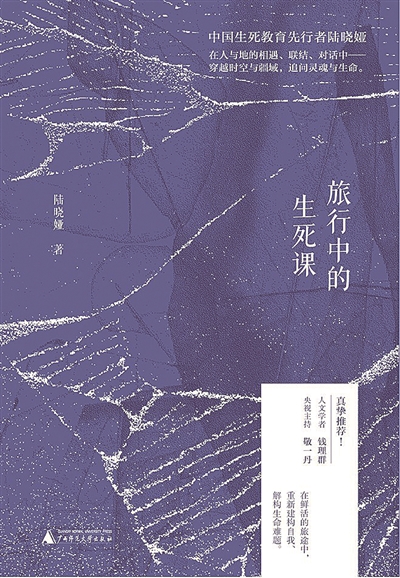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旅行,仅仅是“自由”的代名词吗?基于地理层面的转换为何如此必要,必要到即便过程百感交集,有关异域的想象总是与现实背驰,我们依然乐此不疲?
德国文坛重量级作家马蒂亚斯·波利蒂基在他的旅行随感《美丽、遥远又野性》中试图回答我们的疑问,然而他给出的答案依然如同旅行这件事本身一样缺乏理性:“踏上旅途的行者,要的不是满足,而是幸福,或至少体验一些不幸。他们的渴望是严肃的,意愿是诚挚的,行动是认真的。而这种渴望还有另一面:无论我们去哪里旅行,首要的是远离自己、远离同类,因为我们再一次感到厌倦,厌倦世间万物,而最让我们厌倦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我’压迫并束缚着我们,是那个我们根本不想成为的人。”
相对于波利蒂基感性的旅行意义,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创者段义孚在《浪漫地理学》中有关地理学浪漫属性的阐述,则可以看作是对旅行另一个维度的理性解读。在他看来,地理学关乎对自然和文化的求索,通俗点说,体会险境生还的迷醉感受,探寻自然最深的未知,追索人类文明演进的过往等等,都是地理学的范畴。段义孚认同弗朗西斯·培根的说法——为了避免幽闭恐惧症,人类也许需要将整个宇宙当成游乐场。不过,探索的过程必须与浪漫且先验性的洞察力为伴,若没有对超越人类身体感知的崇高的渴求,就很难取得真正优秀的科学成就。
而这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的专业探索者,每一位携带迁徙漫游基因(一种被科学证明的渴望冒险的遗传基因)的人类都热衷抵达这一地理学的浪漫的崇高。因为,只要踏上旅途,本能的向往便会激励我们,以开放的格局和心态去发现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哪怕那种生活不是更好,异常短暂,但只要不同,就会是一次精神的呼吸,给予原有的生活远观与反思。不论旅行最初的动机为何,它总能够带领我们,抵达思想的某处。
成为旅行者还是游客
笛卡尔曾经形容旅行,“几乎就是和生活在其他世纪的人对话。”因为没什么比旅行观念的转变更能体现人们新近发展出的过度期待了。在人们还能做选择的时候,旅行最古老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看看陌生的事物,人们有种无药可救的渴望,希望去不一样的地方,只基于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无从满足的好奇心。
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幻象》一书中回顾“旅行”的历史——
15世纪,发现美洲、绕非洲航行以及前往印度让人们睁开了眼睛,开阔了思想,并催生了文艺复兴;17世纪,环游欧洲、前往美洲和东方的旅行使人们见识到别样的生活方式,由此引发启蒙运动。曾经,旅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革新的催化剂。它让人思考得更快、想象得更大胆,催生出更热情的渴望。
纵观历史,思想的巨大震动总是发生在旅行的好时代之后。前往远方、见证奇闻逸事刺激着旅行者的想象力。此时的人们似乎更接近于人类探索的本能,也就是段义孚所言的地理学的浪漫的崇高。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图像革命开启,出国旅行的特性开始发生变化。从前,旅行需要长时间筹划,花费极巨,耗时极长。旅行可能威胁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旅行者曾是主动的,现在他变得被动了。旅行不再是体育锻炼,而成了观赏运动。
在现代,旅行设施的倍增、改善及廉价化让更多人能够到达遥远的地方。但前往异地的经历、在当地的经历和从当地带回的经历全都大相径庭了。经历被稀释、被伪造、被预制。这一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描述:旅行者衰落,游客崛起。
在布尔斯廷看来,旅行者是主动的,他费力去寻找人、寻找冒险、寻找经历;游客则是被动的,他期待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是去“观光”,期待一切都替他料理好,为他服务。而我们也从中知晓了travel这个意为旅行的单词,在旧英语里的本义,居然与“折磨”或“问题”是同一个词,足见旅行最初的劳神和费力。“而今天当我们入住星级酒店、打卡网红景区,真的抵达了远方吗?”面对作者的追问,今天马不停蹄的旅行者当做何感想。
城市漫游者的徒步行走
与《幻象》的写作者布尔斯廷一样,被誉为德国作家中的环球旅行者和文学冒险家的马蒂亚斯·波利蒂基,也对今天的旅行充满质疑,他在旅行随感《美丽、遥远又野性》中说,“曾经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无穷秘密和刺激的处女地,等待着我去探索。现在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宝藏之地正在逐年被发掘,终将变得一览无余。……我们这个时代的旅行者常常如中了魔咒,即便不想失望,也在这个全球化世界的诱惑下,不断迈向新的失望。”
即便如此,这位作家还是花了两个章节,特别描摹他的“城市漫游”。“如果人们久久眺望一座城市,就会注意到几个比较突出的城市建筑地标。你会从一个点连到那几个点,并将它们彼此相连。最后人们不仅能享受到远眺带来的愉悦,还会因该城市的建筑规划而感到赏心悦目。如果此时有一张地图在手,就会获益良多。”
他选择不同城市的眺望点:从上海金茂君悦酒店的九重天酒吧向远处眺望,“上海外滩就像玩具街道,人们在欣赏夜景的同时还可以喝上一杯昂贵的鸡尾酒,直到晚上十点半,所有高层建筑上的五彩霓虹突然熄灭。”他也曾在广州塔上,乘坐摩天轮沿着观景台的外沿轨道观美景;在日本大阪的世贸中心大厦的展望台,面向日落的一侧赏夕阳……他说,通过观光塔或是办公大楼的夜景照明,我们可以颇受启发地看到一座城市是如何展现自己的——“首尔和东京会变身为静静地闪闪发光的海洋,在光海里,只有摩天大厦顶尖会有几百个信号灯发出红色的亮光。而在中国的城市里,所有的高楼大厦和桥梁都被挂上了霓虹灯,它们时时变换着不同的形状和绚丽的色彩。”
而比起对于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的记忆,真正给他留下清晰深刻印象的,却是城中被游客们忽视的一个个独特场景,特别是在那里与当地人有过不同方式的交流之后。“我记不清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也对那里大大小小的城堡没有什么印象,这些都是从旅游指南上看到的。但我能准确记起开罗的小巷子,记得那里卖茶的小贩和踢足球的孩子。还有开罗塔希尔广场,虽然交通拥挤混乱,但仍是一块沉闷、宽阔的荒地。闭上眼睛,我还能依稀看见那个友好的科普特人,他每天都在那里摆摊叫卖果汁。有一次,我在他的摊位前把刚喝到嘴里的果汁全部吐了出来(还混杂着其他东西),因为我把一整杯芒果汁一饮而尽。经历过几次这种不幸遭遇后,我才明白,在热带地区不能喝冰镇饮料,至少不要一饮而尽。吐出来的果汁立刻就被尘土吸干了,就好像被蓬松的地毯吸进去了一样,在我们眼前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那些尘土、冷饮摊、科普特人,还有四周明亮耀眼的阳光,就是开罗留给我的印象,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深刻难忘。”
在波利蒂基心目中,城市漫游,经常要走过长长的街道,沿着高大的老城墙或废弃了的工业码头,穿过破败的郊区,或是再走远一点,越过棚户区和高楼大厦之间荒草丛生的空地,都是为了体验旅行尽头那个蕴藏着神明启示的万人瞩目的旅游景点:一棵圣树、一座小巧的陵墓、一面画满了涂鸦的砖墙、一口还是用公牛打水的辘水井。对于那些乘坐出租车直达的游客来说,这些可能毫无意义。然而对那些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到路的行者来说,这幅画面会在他心中留下有力而深刻的印象。
“生活中重要的一切,我们称之为收获的一切,都来自我们的努力和抵抗。”茨威格这句话深深触动着他,“如果我们想对一座城市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就要逐条街道地去攻克它。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城区浪费很多时间,那里其实没有什么可提供给游客的。但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地方能给游客提供一般景区所没有的,即这座城市的常态生活,它的真实面貌,不是为游客刻意准备的或者被游客破坏了的真实面貌。它比其他所有景点都能让人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在这个假期,你可以尝试在一座城市像当地人那样行走。在行走中没有美食的诱惑,也不会窥视四周。不是闲逛,不让自己被驱赶,也不是漫无目的地漫游,只是在徒步行走。让自己加入当地人的运动流,他们的节奏就是你的节奏,他们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旅行中抵达生命的本质
面向广阔天地里的未知,人似乎更容易打开自己。
有读者为《困在记忆里的母亲》这本非虚构作品加了一个副标题——“我的妈妈、我的回忆和一次穿过落基山脉的旅行”。对于作者斯蒂芬·贾格尔而言,这本关于公路旅行的书,实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亦是一场漫长的相识。
因为母亲检查出阿尔兹海默症,女儿决定带她开启一场属于两个人的旅行。为期11天的自驾游,她们共同体验了露营、骑马、徒步、漂流。旅途中,面对母亲的健忘,女儿开始追忆起过往,思考作为女性,疾病、记忆、身份认同在血缘中的传递,以及遗忘与失去,抵抗与妥协意味着什么。
旅行,也创造了更多母女相处、交流与反思的机会。过去那种对母亲的对抗关系,在更多的走入母亲内心后得到了和解,曾经否定母亲的强大,拒绝女性特征的自己,逐渐找到了女性身上的力量。作者意识到:“这次旅行从来都不是为了揭开母亲内心的秘密,而是揭开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抵达命运的深处和生命的本质。
“有时,为了重启或重构新的生活,人们会主动地去打断生活的延续性。”在《旅行中的生死课》中,陆晓娅同样通过旅行,抵达了自己生命的本质。六十岁才开始海外旅行的陆晓娅,曾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退休后创办教育公益机构,在她丰沛的书写里,生命与死亡是线索,串联起时代、地域、风景、人物、文化、历史、文学以及她自己的故事。“旅行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长半衰期’的过程,它在悄悄地重新建构我的精神世界和我的生命。”旅行以及与旅行相关的写作,让她不断建构自我的精神世界,更勇敢地面对人生最后一段生命旅程。
随着年纪的增长,陆晓娅发现自己的好奇心却在不断增长,她成了一个奇怪的旅行者:“看美景吃美食的所谓‘旅游’显然不能满足我,我期待的是旅行中发生更多的事情,它们能让我惊喜、感动、兴奋、悲伤、怅惘、迷惑、战栗……我知道我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花甲背包客’,我更希望在旅途中进行探索,有所发现,让自己心跳加快,甚至眼含热泪。”
在2022年出版的这本《旅行中的生死课》中,散落世界各地的墓碑,穿越时间、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生命力。它们像是索引,让人们有兴趣了解更多逝者的信息。在旅行中思考死亡,似乎过于沉重了,但陆晓娅想让人们面对这无法回避的现实,更深入地思考活在当下的价值。在白骨嶙峋的古代文明遗址上,在阴云低垂浪涛拍岸的悬崖边,在清晨阳光下的乡间墓地,在挂着遗容肖像的名人故居里,在博物馆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前,她让我们与一个个灵魂相遇,也让我们遇见更深的自己。
人少处,万物生
“人少处,万物生”,大自然无疑是旅行的中心议题,它以宽广的胸怀,拥抱并创造一切美好。如伊朗的一位女诗人所说:“我的爱人像大自然,直率,不可抗拒。”
《夏日木屋札记》来自瑞典作家妮娜·波顿,是作家第一部引进国内的作品。她假日住在如《瓦尔登湖》里一般的乡下小木屋,边写作,边打量邻里的小动物。但又不梭罗式地主张离群索居,而是更现代地,张开双臂拥抱新的生活方式。2020年,作者凭借本书,再次入围奥古斯特文学奖决选。
这是一段奇妙有趣的乡间避暑时光。在这片以小木屋为活动中心的生命乐土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共享清凉夏日:与松鼠、狐狸共享居所,与蚂蚁、蜜蜂共享美食,与獾和狐狸无言对视,与榆树、桦树亲切交谈……这些邂逅、互动成就了作者笔下一幅幅温馨有爱的画面。
这是一本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科普小书,展现生命百态,探讨动物与自然的智慧,也启发日常哲思。飞蚁共舞其实是一场盛大的“婚礼”?看似讨厌的乌鸦其实聪明可爱又有同情心?人类有语言,蜜蜂有舞蹈,鸟儿会唱歌,那么植物和细菌如何沟通?……纷繁的生命形态,多彩的自然语言,就是旅行本身的意义。
《万物交响:驴子、随笔与喧嚣》,则是另一场狂野的治愈系郊游,将诗、评论和科学融为一炉,饱含关于人类、世界与爱的诗意。这本奇妙的文学故事集里,里奇以顽皮狡黠的方式观察世间万物,描述的对象从小小的飞蛾到中世纪手抄本上的野兽、花朵,从刺猬的烦忧到蓝莓的善意,从动物到植物,从星空到海洋,从大自然的宁静到喧嚣……书中,现实与神秘共存,科学家与诗人同眠,跳跃俏皮的思绪,在树木、海岛、星辰间闪耀,散发着由内而生的对生活的热爱。
《横断浪途》是七堇年的第12本书,她再次确定了自己对于山的心意。
书中,在寻找仁巴龙冰川的路上,她沿着公路翻上德姆拉山,在山口遇见一场淋漓的雪。明亮、洁净、毫无保留,“茫茫雪原,磅礴似一部白色的歌剧,丝滑的咏叹调。天空亮得令人发盲,仿佛一面无边的银盾。旷阔的尽头,疑似能看到地平线微微弯曲。”在旷野的白里,七堇年觉得自己像羽毛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你又自由又渺小。那是一种安慰。”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