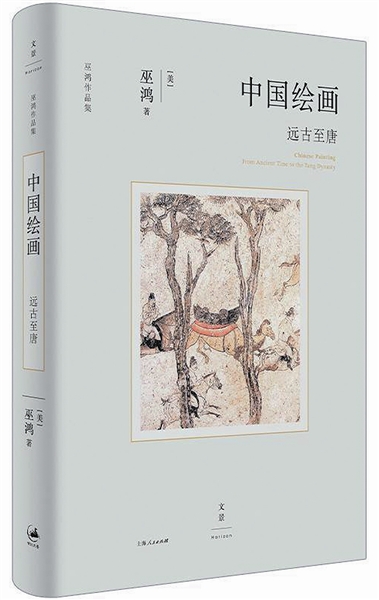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唐末的绘画评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绘画分成若干阶段:“上古”(汉代到三国)、“中古”(晋代到南朝早期)、“下古”(南朝的齐、梁、陈和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近代”(隋至盛唐,或以隋为近代,以唐代为“国朝”)和“今”(中唐之后)。他对这些时代的总评是:“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下古评量科简,稍易辨解”“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
张彦远对“今人之画”的批评反映了盛唐之后的画坛状况:“安史之乱”令盛极一时的唐朝一蹶不振,艺术的创造力衰颓;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毁坏了大量寺庙壁画,严重阻碍了宗教艺术发展;一些文人艺术家则效仿魏晋“竹林七贤”,艺术创作不遵从任何既定规则,甚至流于怪异。
中国绘画三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盛唐成为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早期绘画担负着开发绘画媒材的历史职责,无名画家的集体创作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此之后,以卷轴画为大宗的绘画成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惯性认知……最新出版的《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中,美术史家巫鸿从考古材料出发,带领读者重回远古直至盛唐的中国绘画现场,探寻不同载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画手的风格变迁。
摒弃线性的“进化论”
关于“早期中国绘画”,巫鸿认为它是中国绘画“初期发展阶段”的说法既对也不对。“对”是因为早期绘画和晚期绘画确实有着时间和内涵上的承袭关系;“不对”则是由于这种认识经常暗含着一种进化论观念,将“早期”等同于绘画史上的原始和不发达阶段,有待进化和升华为更高级的艺术表现形式。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试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或南北朝至唐代的雕塑,此后的中国美术史就再也没有产生出同等辉煌的同类作品。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情况当然不是说人类的艺术创造力萎缩或倒退了,而是证明不同时代的艺术有着自己的对象、性格和条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够按照单一的‘进化’概念衡量。”
在巫鸿看来,如果说晚期绘画更多聚焦于对图像风格的自觉探索,那么早期绘画则担负着一个更基本而宏大的职责,即对绘画媒材本身的发现和发明,由此产生出绘画这一绵绵不息的艺术形式。
正如书中开篇所讲到的:鹳鱼石斧图为什么是一幅独立的绘画?因为虽然它被画在一个陶缸上,但创作者实际上只用了这个缸的一面,相当于把一个曲面当成了平面来使用,在概念中把这个曲面展开了,所以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能从一个平面的角度去看它。人类并非从一开始就具备绘画的最基本条件,即承载图像的“平面”。这种平面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然后才有了以二维图像构成的绘画表达。
大量研究表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绘画的平面首先出现在器物和建筑的表面,独立的绘画平面是几千年之后的另一重大发展,从此有了区别于建筑和器物的可移动绘画作品。这种独立绘画从初生到成熟又经历了千年以上的过程,其间发展出手卷、屏风、画幛、立轴等各种样式。早期中国绘画的历史见证了这些绘画媒材的产生和发展。
而后来的独立绘画形式,也始终在与建筑和器物绘画互动:即使是在卷轴画已经相当发达的唐代,杰出画家仍大量创作寺观和宫殿壁画,屏障等室内陈设也仍然是重要的绘画媒介。
“美术考古”与“考古美术”
“美术考古”研究,是利用丰富而系统的田野考古材料,拓宽美术史研究的时间维度和艺术类型,在此基础上,巫鸿进一步提出了“考古美术”的概念,以此进行跨学科创新研究。《中国绘画:远古至唐》这本书脱胎于1997年巫鸿与几位学者合著的《中国绘画三千年》,并增加了诸多考古新材料。不同于中国绘画的传统方式,巫鸿并未预设问题,而是在材料中看各种元素是怎样逐步出现的。读者会发现,书中的大量考古发现例证都曾经出现在课本中。但正如北大艺术学院教授郑岩所言,作者的分析方法却不是我们完全熟悉的,这也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他在这本书里不光教我们知识,同时告诉大家怎么去看一幅画。”
讲到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载体——陶器,巫鸿就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彩画陶器为例。这一时期不同地域的彩陶一般被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两种:河南庙底沟遗址发现的陶盆上,一系列变化的弧形纹和波纹充满了器腹至器口之间的水平装饰带,这些具有动感的纹样引导观者的视线沿器物表面平行移动;陕西绘制半坡陶盆的艺术家则将器物内表严格地分为四等份,绘制两两对称的图像,分割和对称是他们的方式。这两种风格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力求使纹饰和器物的形状相吻合,以增强器物的三维立体感。
类似的具有关联性的实物比对和绘画创作审美异同的分析书中比比皆是,其中特别提及,学者们往往把东周称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复兴”,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哲学的探究、城市的发展,还是视觉艺术的革新,都远远超越以往。巫鸿比对了长沙出土的两幅楚文化帛画: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龙凤仕女图》,画中人物头发以丝带束成螺髻形,眉毛向额角扬起,眼睑之间的圆瞳赋予人物一种凝聚的神情,比起此前时代的人物画,远为写实也更加“风格化”;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图》则是配剑男子形象,正手执缰绳,驾驭一条巨龙或龙舟出行,颈后飘带表达明显动感,龙首上扬,龙尾立一矫健白鹭……
两幅作品主要区别在于艺术水平高下,前者明显出自一位绘画生手,后者则透露了艺术专业训练者对于笔墨韵律的追求。作者还不失时机地引入了一幅同时代希腊壁画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具有一些美术史知识的读者都会发现,此处看到的是中西绘画以后两千年平行发展的起点。
历史上的吴道子竟是“街头艺人”?
书中提到,唐朝朱景玄所著《唐朝名画录》中有关于天宝年间唐玄宗宣召吴道子、李思训一起在大同殿里创作壁画的轶事。巫鸿表示,从历史事实讲,这个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李思训比吴道子年长五十多岁,天宝年间之前已经去世。但作为寓言来读,却别有深意。
其中李思训和吴道子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绘画传统和流派,二人之间的较量反映了不同艺术传统、绘画风格以及画家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异和竞争。
在时人的眼里,吴道子和李思训的风格代表了唐代绘画中的“疏、密”二体,李思训是以青绿山水为代表的密体画风,吴道子则是“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大师。而后者充满动感、富有强烈表现力的绘画并非宫廷产物。吴道子背后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修造佛道寺观的工匠和画匠,与作为皇亲国戚的李思训不同,吴道子出身卑微,从未踏入仕途。史籍对于他的生平记载甚少,只知道他少时孤贫,可能并未接受过正规艺术训练。即使成名后被招入宫廷,其职责也仅限于教习宫人和伺奉皇子,宫廷之外的公共空间才是他的真正用武之地,他的绘画艺术与唐代的大众市井文化不可分割。
文献记载常把吴道子描述成一个街头艺人,当众作画时显示出超人技能,令人称奇。李思训在新、旧《唐书》中皆有传记,而二书对吴道子的事迹只字未提,再次证实了这两位画家所属的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环境。
巫鸿也想以此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现在虽然把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图画形象都称为“绘画”,但这些作品——或是器物上的画像装饰或是建筑上的壁画——在当时都是具有使用价值的,是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环境的一部分。如果脱离了原来的环境或“上下文”的话,它们与其创造者和观赏者的原始联系便被模糊了。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