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启昌
屋檐上整齐挂出一排明晃晃的冰溜子,房屋南墙上依次拴着的蒜辫子、椒串子、谷穗子,还有一嘟噜、一嘟噜来年当种子用的干芸豆、干豆角上统统披了半拃厚的雪粒子。这个当口,裹着寒意的风照例自北往南不依不饶地刮,庭院四周的羊栏、鸡舍、兔笼里出奇静,平日玩皮的小家伙们或站或卧扎堆取暖御寒,用这种无奈的方式迎接如期而至的新年首个日子。村人们没有闲下来,他们在忙着筹备一件事:过阳历年。
小时候,我随父母住乡下,过阳历年的时候庭院里呈现的那帧别有诗意的图景早已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如今,年过半百,虽经光阴洗礼,但记忆中那帧图景的辨识度依然很高。
庄户人不太习惯“元旦”的说法,过元旦都爱说“过阳历年”。现在我从城里回乡下老家时,听街坊邻里还都这么说。像我一样在外打拼的“老乡”回村过元旦都“入乡随俗”地改回说过阳历年,要不,村人会道你“说话拽,脚不沾泥了!”
庄户人过阳历年虽然没有像过阴历年那么正式、那么隆重,但他们不糊弄、不懈怠,毕竟这是新一年的起始之日,新的年份、新的起点,庄户人顺应着祖辈向好的期许,把更好的愿望寄语给阳历年,盼望着自此开始,新的一年五谷丰登、人财两旺。
阳历年这天,寒气肆虐,风抽在脸上疼感强烈。村里的“女当家”们起得早,她们勤劳、贤惠,揉面、切菜、剁肉、煎鱼、包饺子,一项项操持阳历年年饭的营生忙下来,差不多已是晌午。“男当家”们磕了烟锅儿、喝罢茶水,扛起铁锨拉门而出,迎着刷脸的寒风去往北坡、西岭。那里有秋种的冬麦,有窑藏的越冬萝卜、白菜,有暖棚里正在旺长的茄子、辣椒、西红柿,有头年早春定植的蓝莓、火龙果……虽然都苗齐秸壮、防寒无隙,但“男当家”们有心事,半辈子跟土坷垃、跟庄稼稞子打交道,早就养成了“不愿歇下来”的习惯,执一柄铁锨作伴,去自家的“领地”,像将军检阅士兵方队一样,多看几遍自己“统领”的禾苗、菜秧、果子稞,在心中多默念几番好所的话,渴望新的年景更美、更富含诗意。
晌午,香喷喷的菜肴、烧酒,还有热气腾腾的白菜猪肉饺子已上席,村人们各自在家净手洗面,上炕围坐。此刻,庄户人过阳历年的情景卷轴上即将涂染鲜亮浓重的油彩:“男当家”郑重地举起酒杯,跟“女当家”庄重且认真地碰过后,深情地说道:“持家不易。又一年,你受累了!”一句话,情真意切,暖人身心。自城里赶回老家过阳历年的晚辈们簇拥着二老一同举杯:“爹,娘,拉扯俺们,家里坡里,披星戴月,二老辛苦了!”话音没落,酒杯尚在炕中央叮当作响,一家人的眼睛都早已潮濡。此时此刻,一家人彼此相亲相爱的氛围在弥散着酒香菜香饺子香的阳历年的响午愈发浓厚了。
傍晚,村子祥和安静。庄户人过阳历年不像过阴历年放炮放鞭放花儿那么有阵势,但亲戚间、邻居间相互串门道福是传统。晚辈给长辈送吉祥话儿、道福寿康宁;亲戚之间相拥叙旧、嘘寒问暖;邻里之间道收成、谈心事,彼此盘腿坐炕、推心置腹。一个个居家生活、打理日子的好点子在暖意缭绕的热炕头上悄然勾勒生成。
庄户人过阳历年不像城里人那么讲究,有固定的假日,有预订好的酒楼食肆和座席,还有多少件新置的新衣帽新鞋子,或者有搭伴外出冬游。庄户人实在,不圈点不矫情,即使过阳历年话题也离不了土地、离不了庄稼、离不了持家过日子。他们觉得,过日子虚不得、攀不得,毕竟来日方长,得巧规划、善打谱。恰好,过阳历年可以暂时缓下来匆忙的步子,为新日子、新年景做一番铺垫和路演。
时下,我虽远离老家,在城里为生活而舟车劳顿,但心却依然留在老家。我眷恋着抚育我长大的故乡,眷恋着老家庄户人的音容笑貌,眷恋着老家的坡坡岭岭、草草木木,更眷恋着老家庄户人一年一度过阳历年的情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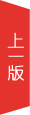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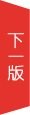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