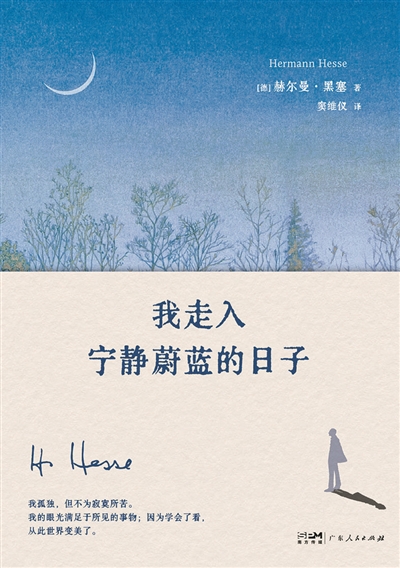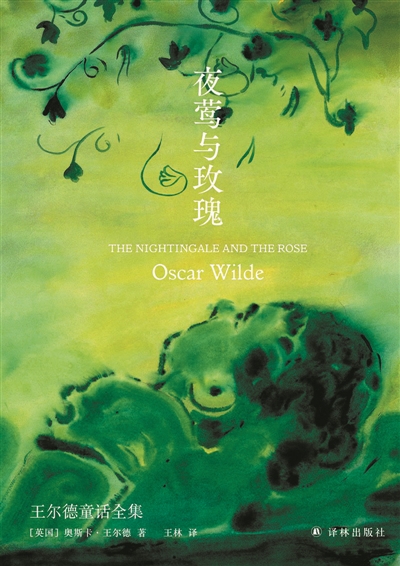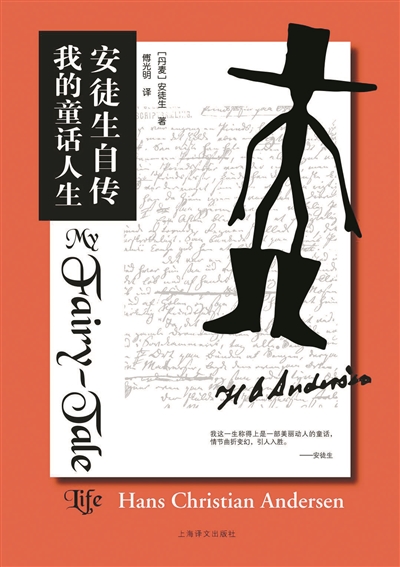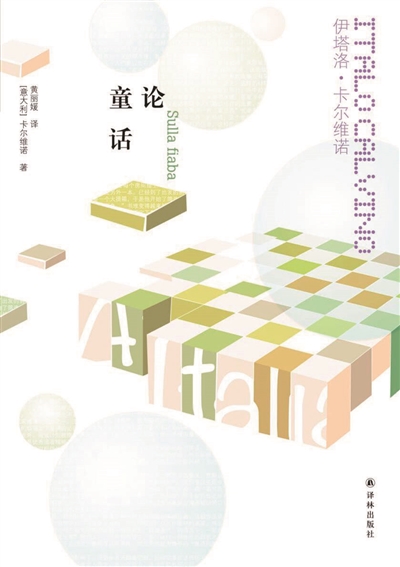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在童话这一几乎被视作童年启蒙的滋养中,有“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之称的安徒生不可或缺。每年的4月2日,全世界的孩子会在阅读中纪念这位伟大作家,他的生日正是“国际儿童图书日”的由来。即便在童书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翻译家叶君健译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也是豆瓣上高达9.5分的无可匹敌的经典。
相隔两个世纪,美好、纯粹、非黑即白的童话世界仍为人类钟爱,善良、勇敢、坚韧、坦诚,这些面对现实生活的优良品质依然保有童话的影子,只是在与世界周旋已久的成年人那里,作为启蒙的童话更多了深层的意味,如同安徒生所说的那样:孩子们只懂得其中的花絮,成年人才能明白其全部。
总有同样堪称大师的后继者不断拓展着童话的边界与况味。安徒生去世两年后,赫尔曼·黑塞出生,以富有哲理的童话寓言故事创造了独属于他的治愈系王国,他将童话看作是揭示生命永恒意义的最佳形式;比黑塞年长24岁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虽然只写下九篇童话,却获得了“童话王子”的美誉,他说写作童话一部分是为孩子,还有一部分是为那些保有孩子般惊奇爱悦之心的成年人,那些能够从简单里品出奇妙韵味的成年人;在20世纪,为意大利童话博取了媲美格林童话威名的伊塔洛·卡尔维诺,将童话的奇幻色彩注入到他的小说叙事,他说过:童话都是真的,无论结局是黑暗还是光明的,重要的是它们都在发生,都在人性的角落里徘徊寄生。
在4月2日这一天与孩子们一起翻开尘封已久的童话篇章吧,它们不同于那些传统意义上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场,又以“从此在一起过着幸福生活”结尾,大师们的童话故事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它不完美,甚至荒诞、虚伪、丑陋,吞噬一切美好,而我们却总会在讲故事的人那里收获爱与希望。
在现实世界里,这些写童话的作家的故事同样充满了如童话般的戏剧色彩,或者说,是他们自己赋予了现实生活童话般的色彩。这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他们的人生如何影响了那些经典童话的走向和趣味,他们又如何将人生的真实与虚妄反转,显露出童话给予我们的通往现实世界的那另一道门。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把天真独特的自我写进童话
在某一个春日,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腓特烈斯贝的公园看到一棵山毛榉树,他突然在那棵树的树叶里发现了自我。“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透明,清新的空气弥漫着一股清香味儿。绿草菁菁,长得很高,鸟儿们在唱歌,我被这一切震慑住了,开始与它们一起沉浸在欢乐之中。我张开双臂,抱住一棵树,亲吻着树皮。那一刻,我全然觉得自己是自然之子。‘你疯了?’一位离我不远的管理人员问我。我惊恐地跑开了,很快,我镇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走回了城里。”在安徒生的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中,他记述了这个看似微小实则重大的人生转折点。
在那一刻,他发现了自我——感性的、天真的、贴近自然的,也是敏感的和脆弱的。或许从那一刻起,他的文学艺术灵感就被自然唤醒了,又或者他的艺术灵感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旅行时被唤醒的:“在‘美第奇的维纳斯’像前驻足良久,我感觉身陷虔诚的艺术奇迹,难以自拔。她从大海的泡沫里升起,洁白、优雅、美丽,她只能是神的创造。在人间,一代埋葬一代,爱情永远不死。爱的女神将永生。”这或许正是《海的女儿》那篇童话的缘起。
这位深爱意大利的丹麦人,以一种超越现实情境的诗意描摹这片土地,就像在书写一个童话般美好的梦境:“在意大利,它的土地和空气充满天国的光彩,美丽的孩子在石松下与我相见,山的胸膛喷出火焰,古老的城市重新复活/在意大利,有穿着大理石长袍的高贵神灵,每一缕呼吸的空气都弥漫着音乐和花香,像油一样的蔚蓝大海广袤无垠,山峦在阳光下闪着七彩光芒/在意大利,一切都如诗如画,随处可见上帝之爱的创造;农家的院落周围,环绕着月桂树和巨大的仙人掌,丰收的葡萄压弯了葡萄架。/在意大利,我有了成熟的思想,却还拥有一颗童心。我认识了自然和艺术。再见,色彩斑斓的土地——我的美梦结束了。”
或许是出身社会底层的缘故,戏剧般跻身上流社会的安徒生始终在荣耀和卑微的落差中煎熬,他的童话故事里也因此透露出很强的忧郁色彩,被看作是自身写照的“丑小鸭”,虽然最后变成了天鹅,但是成长中所经受的打压和排挤从未终止。
不过这并不妨碍安徒生挥洒那与生俱来的天真独特个性,他十七岁时立志写作,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威廉·克里斯蒂安·沃尔特”——“威廉”指代“莎士比亚”,“克里斯蒂安”是他自己,“沃尔特”则是指苏格兰伟大的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威廉·克里斯蒂安·沃尔特”曾经受邀住进狄更斯的家,因把主人妻子礼貌式的挽留当真而搞得不欢而散;他还曾在卢浮宫偶遇巴尔扎克,被他褴褛不堪的穿着吓了一跳,从他身边经过后又转而追上去当面确认他是不是巴尔扎克,实际上几天后他才从朋友那里真正确定,那个人就是巴尔扎克;还有一次,他在旅途中结识了一对有文学艺术修养的夫妇,得知他们拥有一座大房子和图书馆,他果真循着住址找到了对方的家,结果发现了他们住在拥挤阁楼的真相……
安徒生也曾一再自嘲是个个性古怪的人,而他在自传中写下这些细节的同时,便已作实了他不通人情世故的秉性。很难想象现实中如此无法共情的安徒生,笔下的童话故事里却总有触动人心的真切——
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圣诞夜冻死在墙角;美丽善良的小美人鱼为了王子的幸福自我牺牲化成泡沫;坚定的锡兵因天生缺少一条腿被丢进火炉命运多舛……然而悲剧的命运里总有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这些童话人物和他们的创造者同样充满天真,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总是在看似无望的命运中传递爱和希望:小女孩最终在火柴的光亮中与亲人团聚;小美人鱼在完整版的《安徒生童话》里得到天使眷顾,重获永恒的生命;锡兵也在勇敢和坚定的自我认知中走完无怨无悔一生,并让心爱的人看到了自己的一颗真心……他是在以童话的方式蚀刻自己对于真实人生的理解与感悟,理想与憧憬,而我们也最终读懂了他的童话:“孩子们只懂得其中的花絮,而成年人才能明白其全部。”
“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孩子,有多少同时代高贵的优秀男女,对我都很友好、坦率,我对于人类的信任几乎从没有使我感到失望,即使艰难岁月也包含着幸福的因素。我觉得,我所经受的不公正,以及妨碍我发展的行为,最终都给我带来了美好的结果。”他的童话因此照进了现实。
赫尔曼·黑塞:
用童话揭示生命的永恒意义
热爱童话的人一定是亲近自然的人,安徒生如此,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赫尔曼·黑塞也是如此。“我的先生们就是苹果树、雨和太阳、小河和森林、蜜蜂和甲虫、牧神潘恩和外祖父宝藏箱里跳舞的神像。”
童年黑塞就已经在自然与精神的契合之中,学到了生命中最不可或缺和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痛恨物质社会、工业文明,作为传统的古典浪漫主义者,他享受田园自然。和他小说中的主角“悉达多”“荒原狼”“克莱因”“德米安”一样,他是求知者,是不满足于表面现象的人,他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以获得精神的成长,寻求世界的终极答案。而他发现,童话奇诡的想象力正是揭示生命永恒意义的最佳形式。
黑塞的童话同样关于精神的成长与救赎。在完成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东方之行后,他写下童话《诗人》。讲述诗人韩甫在河边的一场灯会上偶遇了一位深谙诗道的十全辞师的故事。他随师父山中学艺,不知岁月飞度,亲故渺茫,再遇灯会,思绪流转,竟无法区分水中花灯与现实中的花灯……《笛梦》《神秘的山》《奥古斯图斯》都是关于精神的成长与探索,主人公都在如迷雾般的生命中踽踽前行,深刻体悟人世的孤单与寂寞,他的童话即是对生命之苦的咏叹。
1916年,父亲的离世和看似无休止的战争让已逾不惑之年的黑塞遭遇重创,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疗愈之路异常艰难——阳光在一点一点退却,留下就只能忍受谷底阴暗寒冷的煎熬,童话《难走的路》就是此时作家内心的写照。童话写作,成为黑塞自我救赎与疗愈的方式,其中《一长串的梦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游历波谲云诡的意识世界,探索日常中被压制和约束的另一个“我”。从此时起,童话成为黑塞向内寻求生命意义的方式,他童话中的主人公——年迈的高山、固执的藤椅、骄傲的少年、丑陋的矮人——所有生命全都在一场杂沓的无法摆脱的困境中活着。
在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的学生约瑟夫·朗博士的建议下,1919年,黑塞去到风景秀丽的提契诺,《我走入宁静蔚蓝的日子》这部随笔集记述了这段疗愈旅程,作家在这里远离过去生活的梦魇,他承认,这场自我治疗是成功的。自然再度赋予了他巨大的能量,《悉达多》《荒原狼》等重要人生作品,都在此间完成,最终成就了这位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翻阅这本随笔集,黑塞用他虔诚的态度和精细入微的观察,捕获大自然的勃勃生机,驱散心中的阴郁,获得内心的宁静,他屡屡提及那些对他形成治愈的东西:自我意识、东方思想和绘画。而他用画笔展示的提契诺风景,也如同童话世界一般色彩斑斓,诗意盎然,让人联想起他童年时进入的智慧化身的外祖父的书房,各种神秘的异国宝藏曾经为他的童年生活罩染了一层彩色玻璃糖纸般的光彩,让他感觉自己就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里世界”的魔术师。这位最受全球青年爱戴的心灵挚友,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危机,探索自我完善的道路,重回纯真无邪的状态,结果却探到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并在100年后依然释放着疗愈的能量,他解读自己的能量之源:“我的眼光满足于所见的事物;因为学会了看,从此世界变美了。”
奥斯卡·王尔德:
以童话传达艺术之美
博尔赫斯曾经这样评价王尔德:“千年文学产生了远比王尔德复杂或更有想象力的作者,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魅力。无论是随意交谈还是和朋友相处,无论是在幸福的年月还是身处逆境,王尔德同样富有魅力。他留下的一行行文字至今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王尔德,以文字的纯正精致之美为世界熟知,人们称他的作品瑰丽华美,也包括他为数不多的童话。据说王尔德一生一共写作了九篇童话作品,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他的童话短小惊艳,总是笼罩着或深或浅的哀伤,又包孕着真善美的坚韧力量。有人说,王尔德的文字,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童话,每一篇都体现着对于艺术的竭力追求,体现着敏于体察并呈现美的玲珑文心。美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埃尔曼所写的传记《奥斯卡·王尔德》中讲过一个故事,当初《道林·格雷的画像》出版时,出版商出于商业考虑,曾要求王尔德将小说扩展到十万个单词的篇幅,王尔德回复说:“英语中找不出十万个优美词汇。”据说后来增补版,仍不足八万个单词,正所谓字字珠玑。
王尔德之所以写作童话,据他自己说,“一部分是为孩子,一部分是为那些保有孩子般惊奇爱悦之心的成年人,能够从简单里品出奇妙韵味的成年人”,他曾经十分具体地将自己童话作品的阅读人群确定为“18岁到80岁之间所有充满童真的人”。的确,他的童话老少咸宜,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够从中得到爱与美的滋养。
王尔德童话的译者张炽恒表示,“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并非唯有美,而且饱含着爱和悲悯,无论是为他人献身的善良的“快乐王子”还是为了成全所谓的爱情而献出生命的夜莺,传递的都是温暖的悲情,而身为大戏剧家的他,尤其擅于讲故事,并在故事中将美和讽喻完美结合。“小时候看安徒生童话,长大了就看王尔德的童话。”此言不虚,毕竟,谁能够拒绝精致的艺术之美呢。
伊塔洛·卡尔维诺:
把童话作为文学的方法
进入20世纪,对于民间童话的收集与整理似乎成为众多写作者的传承,比如,编纂了《意大利童话》的卡尔维诺,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书写的《精怪故事集》,波兰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等等。而与其他人的编写不同,卡尔维诺更关注童话原始的、反逻辑的元素,他认为这些东西更有意义。相反,逻辑上的贯通,反而会改变童话的原生状态,让它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越来越乏味。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有很多突兀的东西在里面,保持着一种很奇特的味道。
这也正是卡尔维诺的写作观:不要密不透风的逻辑关系下的世界,而是带着诸多可能性、不可预知性、突兀性、偶然性。童话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不合逻辑性,因此神秘的东西才出现。
卡尔维诺在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这本讲述游击队战争经历的小说,主人公皮恩的名字正是童话里的木偶匹诺曹的昵称。然而卡尔维诺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的童话色彩,直到他的好友切萨雷·帕韦泽指出这一点。“在我渴望建立的新文学思想中,有一个空间,要让我从小就着迷的所有文学世界复活……这样,我就开始写像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那样的小说,也想写像史蒂文森《金银岛》那样的书……帕韦泽第一个向我谈起我作品中的童话笔调,在这之前我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并尽量确认它的定义。”
卡尔维诺曾用两年时间收集资料、将童话分类并比对不同版本,他从未感觉到枯燥:“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充斥着一种昆虫学家的热情……这是一种会迅速转变为癖好的热情,为此我宁愿用普鲁斯特的全套作品去交换一个《拉金子的驴》的新版本……”卡尔维诺对童话倾注的热情并非来自对童年、儿时读物的怀念,而是源自童话与他的人生哲学及美学判断之间的共通之处。对此,他这样说道:“对世界的伟大阐释总是看起来像童话或乌托邦。我们可以说,接受世界本身状态的作家将是自然主义作家,不接受世界本身状态但希望对世界进行阐释并将其改变的作家将是童话作家。”
1963年,卡尔维诺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极具童话色彩的小说集《马可瓦尔多》。讲述在城市里生活的贫穷工人马可瓦尔多的五个四季。这是卡尔维诺笔下又一个抽离于周遭环境的、有趣味的、纯真的人,在灰色的城市的缝隙中发现蘑菇。他在用童话的方式书写城市生活可能具有的诗意与超然。
卡尔维诺在《论童话》中说,“童话包含了对这个世界的全面阐释,丑陋的,美好的,都在里头,而即便是面对那些最可怕的魔力,我们也总能找到办法来摆脱它们。”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