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梁
有关临终关怀的影片并不在少数,比如《温暖的告别》《失控的生命》《心灵病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入殓师》。与之主题不同却更加令人感慨的另一部电影是《死亡护理师》。这部颇具争议的影片,通过完全相悖的视角,揭露出临终关怀的终极探索,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真爱?
主人公斯波在一家护理公司工作。他和同事们主要的工作是照料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在儿女因生活压力所迫无法照顾老人的情况下,护理公司的出现给了他们生活上的缓冲。在那里,工作人员会为老人检查身体、整理家务、洗漱料理,甚至为死去的老人守灵。斯波的护理水准堪称楷模,对待老人,他总是笑脸相迎,任劳任怨,被新入职的同事奉为典范。一切看似平常,一切又都暗流涌动。一位老人意外离世,勾起一桩惊人的谋杀案,四十多位老人死在斯波的手上。面对检察官讯问时,他却平静地说:“我拯救了他们。”因为在斯波看来,这些老人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家人的嫌弃,对他们而言,自己不再是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甚至无数次想离开这个世界。
斯波的怪异思想和行为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小被父亲带大,父亲衰老后,他决定尽一切可能为父亲尽孝。但随着父亲病情加重,斯波再也无力照顾他,甚至无法去上班,申请低保也不被允许。偶尔有一次父亲处于清醒状态,他对斯波说:“你帮我个忙,杀了我吧。我不想这么活下去了。”斯波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通过注射尼古丁结束了父亲的生命。侥幸逃过警察检查的他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使命,于是以同样方式结束了41位他照料过的老人的生命。
女检察官大友了解到,斯波通过监控发现这些被照料者的痛苦,他们不仅要忍受病痛折磨,还带给家人无尽的伤痛。他们的“活着”,已经背离正常人的轨道,成为负担。在斯波看来,如果不结束,就无法重新开始。就像影片中的羽村一家。羽村既要照料年幼的孩子,还要去打工,还得照顾近乎癫狂的母亲,这种生活让她濒临崩溃。母亲的离世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虽然是以谋杀达到目的。
影片没有设置悬念,在大友检察官逼问下,斯波很快承认了杀人。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错,他不仅拯救了即将死去的老人,也拯救了活着的人,让他们不再受亲情羁绊,重新好好地活着。但在大友看来,再多堂而皇之的借口都是在为谋杀找托词,人的生命岂能随随便便就被别人剥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虽然赞成安乐死,但也不赞同假借他人之手。安乐死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从法律角度,前者更倾向于无罪,而后者则往往被判定为谋杀。影片中,斯波的行为就是一种积极的安乐死行为。
大友的母亲患老年痴呆,无法照顾自己。被斯波称为在“安全地带”的大友把母亲送到了条件完善的养老院。但女儿最终也明白,其实母亲并不愿意待在养老院,只是想为女儿减轻负担。斯波为父亲注射完尼古丁后,从父亲的枕头下找到一枚千纸鹤,上面写着:“感谢你做我的儿子。”可见,父亲并不想离开斯波,但又不想因为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拖垮儿子,他想让儿子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们在谈生命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想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点。我们并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活”有着前因后果,不仅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更给了自己的孩子以生命。在生命与生命交错延续的过程中,爱便诞生了,成为我们维持生命的强大营养。但爱同时也是脆弱的,在残酷的生活中,爱会变得沉重、破碎乃至模糊。但爱从不会消失,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改变了面貌。
我们讨论人“生而为人”,其实说的是“社会人”的概念。即这个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可以拥有人所应具有的一切权利包括生存的尊严。一旦脱离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属性,那这个所谓的“人”,起码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被定义的人。
《死亡护理师》所讨论的,恰恰是“人”与“非人”的模糊地带,也是对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的终极拷问。“与其如何,还不如怎样”是积极者的逻辑,而“即便是如何,又能怎样”是消极者的依据。就像人不能选择“生”一样,对于死亡的选择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人既然身处社会,必然要受到法律、道德等约束。很多事情的对错,无法通过简单的表象去判断甚至做决定。之所以人类社会还在继续向前,是因为总有一些事情值得期盼。就像电影《入殓师》中说的:“我送走一个又一个人独自离开,逝去并非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路上小心,总会再见的。”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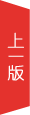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