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外考察的路上,我习惯于发一些感慨,并随手记下一些零星的思悟片羽,它们是每一篇文字的种子,只需要一个春天和一场雨水就能发芽。”
这场春雨在2022年落下。躲在青岛西海岸书斋里的周蓬桦,不停地回放和反刍十多年的田野考察经历,一些场景和画面愈发生动,于是开始撰写《乌乡薄暮》。“也许是由于年龄原因,较之以往的作品,这本书相对要成熟许多,想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关于物质,关于精神,关于当下的生存环境,关于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在202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周蓬桦的《乌乡薄暮》出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新书推荐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曾在2024年全国高考试题中出现的《霜降夜》也收录其中。
到荒野中去,与世俗保持恰当距离
“在我看来,荒野是大地的词根,是精神最早的出发地。只有置身于野地荒天的背景下,才会让人感到天地的苍茫悠远,时间像一个幽暗的黑洞,而人是如此卑微渺小。”
十年以前,“精力充沛,还有野心”的周蓬桦几乎每年夏天,都要打点行装到东北山林和荒野草原去,并在当地文友的帮助下,在长白山区建立了写作营。“因为我太喜欢森林的幽寂和草原天高地阔的感觉了,与世俗保持恰当的距离一直是我之所愿。”
为何钟情于东北森林和草原牧场?周蓬桦解释这里有一个家族背景原因。多年前他的祖先曾经尾随山东闯关东的大军在白山黑水间落脚谋生。“我的父亲是在东北出生的,东北至今还有许多亲戚在那里生活。说真的,我喜欢东北的开阔地貌——无垠的森林和草原,那里是我的另一个故乡。”当周蓬桦的写作“快要把鲁西平原开采尽了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重返东北,“童年的记忆瞬间复活,感觉满目都是新鲜。让我的写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周蓬桦看来,东北大地的风情与山东的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较大区别,“对我而言,则有了一种比较和参照,让文本有了‘异质感’和‘陌生感’,文字里仿佛被注入了野性能量,有一种扑面而至的‘野生感’。”
在荒野中行走,周蓬桦记录下一些见闻与感受的片段,记录下那些风雨那些冰雪,还会在现场采集一些实物标本,如石头、树皮、植物之类,“这些一手资料相当重要,结束考察后,我会带回书房逐一进行研究,获取写作灵感,从中寻找观察事物的新角度。”
唤醒人们对天地万物的共情之心
在《乌乡薄暮》中,读者会从扑面而来的松木清香和野趣横生的细节中,找到神秘古怪的林间传说和当下人与自然的深层哲学思考。周蓬桦用诗人的目光和诗性语言多角度解读世界,向读者传达温暖、恒久与美善能量。周蓬桦认为:“写出自然界以及生灵的现状与处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建立链接起来,唤醒人们对天地万物的共情之心,这是自然写作的价值主旨所在。”
“自然写作首先是文学,是为了方便人的阅读,细雨润物绵绵渗透,并从中受到启发,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思考兴趣,进而把对自然的敬惜之心唤醒或激活。”周蓬桦尽量避免在文章中搬用一些地理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的专业词汇,而是尽可能把对自然的写作进行过滤发酵,达到常识化和亲切化。遇到一些绕不开的知识点时才求助于典籍,以避免出错。他强调:“书写自然并非肤浅的自然景观照录,即便描述一朵花一株草,一只小松鼠每天在洞穴里的活动轨迹,也是有着深刻的用意,让人有所警示,唤醒沉睡的悲悯:不能再无休止地破坏下去,这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与具体的个人息息相关。”
偏重于讲述自然与人的关系
《乌乡薄暮》的责任编辑沙爽说,周蓬桦的新作与法国作家西尔万·泰松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气息“一脉相承”。而周蓬桦坦言此前并未读过此书。后来,他网购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细心读完,“感觉自己与西尔万·泰松在生活观念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不奇怪——两颗热爱自然的心是相融相通的。”周蓬桦也很明晰地分析,泰松是偏向“本我”的,偏向个体融入自然的感受,而《乌乡薄暮》则偏重于讲述自然与人的关系,写自然界对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一旦背离常识就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灾害与损失。
提起自然写作,周蓬桦和很多读者一样,会说起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等。但关于自然写作所要传达的要义,周蓬桦也有东方解释,其实老子和庄子在其思想学说中就阐述过,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上善若水”等,“人类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只能在局部改造自然,用心去呵护与善待,当遇到利益冲突之时,应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给后人留下一块阴凉,再者就是享受自然给予的抚慰,告别狭隘、苟且、自私和自以为是。”周蓬桦借用散文家苇岸的话总结,去做一个“人类的增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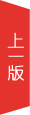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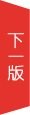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