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鹏
春节后的一场大雪,“千树万树梨花开”,让小城真正有了北国风光的诗意。我渴望雪后的山村,蛰伏的心追逐着风儿,踩着一路雪霜,去看雪晴云淡的南九水,给自己一段款款的时光。
这是一片喧嚣里的原乡,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不陌生,我的青春曾与溪水里的波光粼粼一同闪烁,无数次信步山林,听布谷催春,看樱桃红晕,摘几朵陌上花,拾几颗鹅卵石。于山村的四季,我更喜欢这里的冬天和冬天里的雪。
雪后的山村,皑皑白雪覆盖在温柔起伏的大山上,银装素裹,参差的房瓦上仍留有几分雪意,禾苗、柴堆被雪完全覆盖,昭示着这里的雪似乎比城里大许多。老槐树枝杈上还有几只看家的雀儿,正蹦来蹦去,振落在枝上的积雪,脖颈处的细绒羽毛被风吹逆起来,俨如我新买的那条围巾。依然是那条小巷,磨盘上蹲着一只小黄猫,周围留着浅浅的脚印,似朵朵梅花的影子。河中突兀的石头像几只白虎趴在雪地里,惺忪起来,正要呼啸山林。几朵不知名的野花脸上,雪花正在化作水滴,阳光映衬下像涂着淡淡的胭脂,装扮着花儿,在徐徐吹来的微风中晃动着脑袋,摇曳着身姿,正跳着一支迎接春天的舞。置身一个白色的童话世界,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心灵都在净化。我想,生命的美好就藏在这种自然和平静中,无需刻意追求,无需过分在意,只要像雪一样无声无息,就能感受到生命的韵律和美好。正如杨绛先生所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走在山路上,“咯吱”的踏雪声轻轻回荡在山谷中,这里是百年老路台柳路的尽头,一个叫柳树台的地方,著名的崂山大饭店和麦克伦堡遗址被大雪覆盖着,往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我熟悉这里的春夏秋冬,也熟知崂山的许多传说掌故,都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亲口告诉我的。记得上世纪末的某一个冬日,我刚到乡下工作不久,一场漫天大雪挡住了回家的路,村支书幽默地说,人不留客天留客。拗不过他们的热情,我索性就住在山上。我跟着书记到屋后菜地里拔了一颗白菜,只见他左手抖落掉菜帮上的雪花,右手抱着一捆柴火,哼着茂腔来到灶台。村书记做得一手好菜,那是我平生吃到的最鲜美的白菜水饺,第一次品尝到拳头菜、山蘑炖土鸡、老虎菜。伴着噼啪的灶火,听他讲述竹窝村的前世今生,台柳路的历史渊源,听他讲述村里的石匠们开采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的故事,还有他开山打石头又承包山林的创业史。这个雪夜,我体会到了山里人像雪一样朴实无华的秉性。伴随着窗外的雪花,酒意潮红了我的脸颊,我觉得整个山村都悠悠然的微醺。20多年过去了,如今老书记的儿子带领乡亲们已经把采石村转型为民宿画家村,九水深处有墨香,我喜欢那幅《山村雪晴》的水粉画,这是飘在雪花里的记忆,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时代缩影。
山路深深处,心境陷入一片鲜活的宁静中。突然,一阵风吹过,松叶上的雪飞落下来,像缤纷的心语,像云朵的碎末,擦过我的脸颊,我伸出双掌,想尝试触摸那份超凡脱俗的美丽,她们或从指间滑落,或瞬间化作一滴透明的水珠。我想起儿子小时候玩雪的童趣,把雪花说成白糖,那是他舌尖上最初的味蕾,与雪花一次天真无邪的初见。如今,儿子身在远方,我告诉他故乡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飞扬的雪花只能化作淡淡的乡愁,飘逸的情愫是父子十多年来短暂又深情的陪伴。冬日的雪花,曾经开得那么绚烂,虽然只是一刹那的美好,但在我的心里却是永久的。我默念,那就让人间的美好收纳于心中,无关时间的长短,好好珍惜渐行渐远的风景和人生。
终于登上山顶,抬头望着天空,暖暖的阳光照在雪映的群山,远处灰蒙蒙的树枝笼着白色的雪,就象一幕萦绕在村庄周围的袅袅炊烟。此刻,我怀揣着一颗宁静的心,去聆听大雪的清音,去感受万物的枯荣,我问自己,一生能看几次冬季里的“花开花落”?我对一场雪有了更深沉的感悟:雪花的姗姗降临,雪花的凋零谢幕,都是那么从容和轻盈,是在用无声语言告诉我们,不卑不亢,做一个有度的人,不争不抢,做一个温和的人,无声无息、默默无闻才是雪花的精神之美。正像山里人常说的那句话,人要像石头一样实诚。大雪无印,大雪也有痕,雪融化时,一切真容都会显现,或高尚、或丑陋。我鄙视那些“嚼舌头”的人,雪融化后是一汪清水,能映照出人世间一切肮脏的灵魂,我更希望掬一捧雪水洗濯藏污纳垢的地方。
太阳下山了,我该告别小山村了,告别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余辉下的雪影和微笑都是那么灿烂。或许山村不能常常相见,但乡情却厚植心中,生长成长长的念想,那洁白的雪花永远在脑际飘洒,那雪地里的小路永远在记忆里蜿蜒,那一张张笑脸永远定格在我感光的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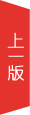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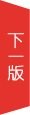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