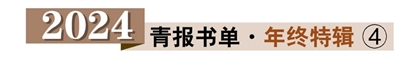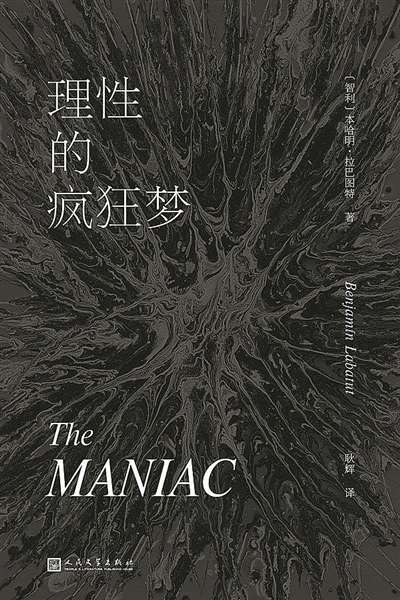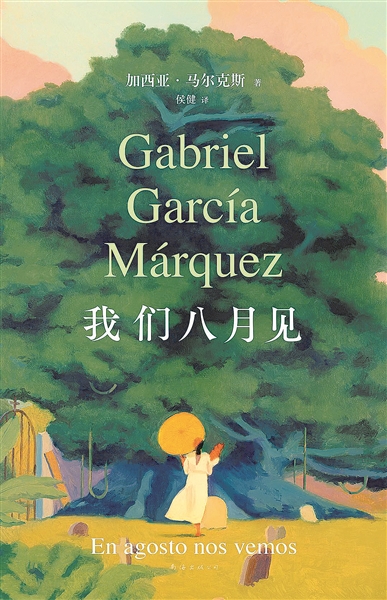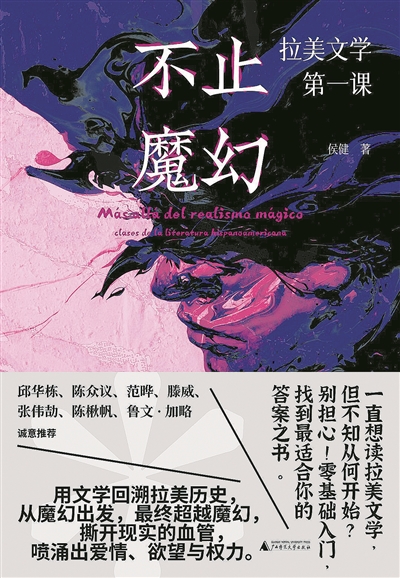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2024年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逝世10周年,他的遗作,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我们八月见》全球同步首发,奈飞剧版《百年孤独》也在这一年热播,似乎成为重新点燃我们对于拉美文学作家热情的一条引信。
尽管属于“拉美文学爆炸”的一代作家已渐行渐远,他们的作品却始终陪伴着我们,常读常新,这一年,在《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中,我们重新与十位奠定拉美文学世界文坛地位的巨匠相遇,他们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重新思考和描摹现实,正如马尔克斯所言,他们“共同书写了一本关于拉丁美洲整体现实的全景小说”,创造了一个具有拉美印记的独特的文学世界,从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和方式。
这一年“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有多火?从青岛籍译者侯健在2024年推出的译著及专著即可窥一斑: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遗作《我们八月见》,全球首个翻译版本的大部头《略萨谈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在9月面世;还有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圣马利亚三部曲”《短暂的生命》《造船厂》《收尸人》,以及略萨的传记《写作之癖》出版;《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他也是译者之一;此外,上半年还出版了作为拉美文学入门读物的个人专著《不止魔幻:拉美文学第一课》。在侯健用西班牙语出版的另一部学术专著《西语文学汉译史(1915-2020)》的尾声部分,他用“西语文学汉译‘爆炸’”来形容西语文学近年来在中国的译介现状,并在一次采访中坦陈,如今人们对于拉美文学的关注度堪比20世纪80年代拉美文学译介的火热态势。
正如侯健的拉美文学“知识普及读本”《不止魔幻》的标题,拉美文学远不止于魔幻现实主义,亦从未止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爆炸期,这其中最不可或缺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这位被读者理解为“拉丁美洲的T.S.艾略特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家,他的“散论”《在地狱阅览室里》在2024年面世,其间他以更加真实的面目袒露心声,直抒好恶,让我们看到他曾经创造的文学世界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当然,必须提及的还有一位“80后”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凭借《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他在2022年以黑马的姿态给中国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次他延续了对真实历史人物“离谱”的虚构这一“诡异”叙事风格,依旧在虚实之间高清还原科学家惊心动魄的一生,这次的主角是人工智能之父冯·诺依曼。
拉美作家们用风格迥异的作品始终突破和拓展着拉美文学的边界,这种努力也使得任何试图草率定义拉美文学的行为成为徒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让读者看到了一条属于自我的独特路径,选择这条路径需要勇气,而对于这一地域的作家而言,勇气即是一种本能,亦是使命。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在拉美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找到独特的“自我”,使之演化为一种自我激励,而重要的是继续阅读,重新阅读。
在此引用波拉尼奥在1998年写下奇异巨著《2666》之际面对《巴黎评论》所言,为2024年收官:“我为那些阅读科塔萨尔和帕拉(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的钢铁般的年轻人所感动,就像我阅读它们并打算继续阅读一样,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书是世上最好的枕头。”
重温拉美“文学爆炸”时代的作家
20世纪60年代,路易斯·哈斯为即将改变历史的文学现象——拉美“文学爆炸”确立了正典,奠定了基调。在《我们的作家》一书中,他将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罗萨、奥内蒂、科塔萨尔、鲁尔福、富恩特斯、马尔克斯和略萨,纳入“拉美文坛十圣”,“他们利用文字来表达自由的内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以及谈论现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但也都是同一个虚构世界的一部分。这里有传统,也有新传统的开始。”他将此确定为拉丁美洲小说艺术真正诞生的纪年,而此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尚未面世。
预言者的预判并非枯燥的评论,如肖像小传般的精妙描写和不避锋芒的评语归纳,显然对于那些只识得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文学“小白”也极度友好。这本入门书给予了大众阅读者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拉美所谓“神奇的现实”。如哈斯所说:“这些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充满压迫和审查、流亡和漠视、破坏文化的极左或是极右的暴政,或是由官方文化机构设置的精神官僚主义等的环境中脱离出来,疾呼道:存在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声音,让我们在思考和生活中说话,或是让我们在梦中诉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是不同的。”
重新思考,重新创造一切,这是“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给予我们的共识。在文学博士、译者侯健出版于2024年的《不止魔幻:拉美文学第一课》中,为入门者揭示了拉美小说的演变历程:19世纪出现之初的规律是“模仿”,模仿西方的流浪汉小说,模仿浪漫主义小说等等;到20世纪的前三十年,拉美小说的规律是“自我”,写别人没有而只有我有的东西,例如墨西哥革命小说、土著主义文学、大地主义文学等等;进入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乃至文学爆炸时期,拉美文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刻,侯健用“整体性”来概括其特征;在厘清上述脉络之后,作者还推介了活跃在新世纪的拉美青年作家。这本书脱胎于此前侯健在B站开设的拉美小说课,课程的主题为“魔幻、爱情与权力”,在侯健看来,普通读者对于拉美小说普遍有一种误读,那就是将其简单概括为魔幻现实主义,无论视频课还是这本书,他都希望纠正这一误读。而在书中,侯健对于拉美文学最终的定论是,“没有规律才是当今拉美文学的最大规律。”
两位“文学爆炸主将”间的对垒
2024年拉美文学出版的大事件,恐怕要属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99读书人”出版的《略萨谈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这部大部头了。这是本书在全球出版的首个翻译版本,此前,这本马尔克斯研究领域的重要专著曾被作者略萨雪藏近半个世纪,这次是首度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出版。
此书中译本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略萨对另一位“主将”马尔克斯的研究成果,更在于它弥补了学界和出版界空白,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在拉丁美洲文学的出版、研究、翻译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关于“弑神者”名称的由来,译者侯健在一次新书分享活动中提及:马尔克斯曾在自传里讲述,他对于故乡的眷恋,故乡一直是他心灵的支撑,而少年时他陪母亲回到故乡去卖房子,发现这种支撑不复存在了。自己的乌托邦被毁,那就创造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小说家总要摆脱神明给予人类的宿命,去创造一个自我的新世界。这正如同取代了神明对于人类的权威一般。而书写此书的略萨则是另一个“弑神者”,要向我们打开马尔克斯的文学世界,乃至精神世界。
略萨在书中的书写并没有流于评论家的理论化评述,而是细致入微地拆解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并对他的每一部作品进行了细读。他告诉我们: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宇宙是如何搭建于现实和虚构的合力之上的;后者的故事有多少源于他一直想要表现的童年经历,就如同他刻意使用的小时候外婆给他讲鬼故事的口吻;又有多少源于欧美现代文学的传统,他试图在索福克勒斯、福克纳、海明威,以及马尔克斯最喜欢的拉美文学作家鲁尔福那里找到马尔克斯小说的源起,让我们思考,小说到底是什么,所谓现实和虚构是否能截然分开……
略萨在向我们说明,伟大的小说是如何写出来的,马尔克斯如何成为马尔克斯,这是普通的评论家做不到的,而是两位大师之间的一次间接对话。一位重量级作家为另外一位已经成名的重量级作家,野心勃勃且充满自信地写就一部大部头,显然有些匪夷所思,而这更增加了这本书的独特性。
当然,关于略萨和马尔克斯由好友到反目的谜团,也为这本书增加了八卦的卖点。关于这段历史公案的真相,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个性迥异而又旗鼓相当的二人,似乎注定不会成为好友。略萨就曾在书中流露,采访马尔克斯时,他经常信马由缰,如提到马尔克斯的小说,似乎与骑士小说的传统有某种关联时,后者立马认同了略萨的这一猜测,这反倒让略萨对此生疑。相对于略萨的严谨追求细节的态度,马尔克斯显然不修边幅。在今年出版的《巴尔加斯·略萨:写作之癖》中就有一例:有一次,三位西班牙作家到略萨家中做客,他们想见见马尔克斯,于是略萨邀请了这位邻居,没想到马尔克斯穿着写作时习惯穿的工装和一双颜色不一样的袜子就来了,略萨当场就显得有些不快……同为现代经典作家,略萨与马尔克斯对于世界保持着各自独特而又新鲜的认知,而这种新鲜的认知又是建立在各自强大的个性基础上的,这让他们即便对对方有高度的认同,也很难走到一处,正如双鱼座和白羊座之间很难和谐。这也是译者侯健与作家、评论家赵松在一次分享活动中的共识。
重新认识小说之外的波拉尼奥
今年出版的中文版新书《在地狱阅览室里》,最初常被读者误认为作家波拉尼奥的另一部新奇的小说,而实际上,它是作家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全集,书名源于作家的一首诗作的名称。尽管收录的文章主题各式各样,但全书始终存在一个统一的波拉尼奥式的语调:那是一种既宏大又浪漫、既深刻又愤世嫉俗、既尖刻又轻率冒犯的语调。
波拉尼奥的评论中没有精英主义,只有文学标准,对于某些通俗文学作家他也不吝赞美,比如《汉尼拔》的作者托马斯·哈里斯,波拉尼奥评价他算不上是伟大的作家,但能把故事写得如此引人入胜已经很了不起。
他会评价卡夫卡:“卡夫卡明白旅行、性爱和书籍是三条不通往任何地方的死路,然而它们也是三条值得投身的道路,值得迷失在途中的道路,从中人们能够重新找到自己,或者找到某种东西,随便什么东西,一本书,一个动作,一件遗失物,找到任何事物或者是找到一种方法,如果走运的话可以找到“新奇”——那个始终在那里的东西。”他也慷慨地向读者分享自己对科幻文学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继承自马克·吐温等美国文学的叙事技巧的赏识。
谈到他不喜欢的智利小说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时,他则表现出恶毒的直言不讳:阿连德的作品虽然糟糕,但它是鲜活的;虽然枯槁贫血,同许多拉丁美洲人一样,但它是鲜活的。它虽然活不久,如同许多病人一样,但当下还是活着的。而且,奇迹总会发生。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胡安娜·伊内丝·德拉克鲁兹修女会在她面前显灵,给她列一份书单。
编者对于书中的文章给予了特别的分类:回忆性质的文章、欺负别的智利作家的文章、伪装成散文的短篇小说、个人诗学陈述、重读经典、发掘新人、夸赞朋友、无法归类、正式讲稿。这其中包括了7年的评论、日记、“读过”和“看过”,间杂生活片断的“广播”,对喜爱的书和作家,献上泛滥成灾的赞美,对讨厌的一方则不留情面和口德。所有这些看似无意义的琐碎汇集起来,便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意义——勾勒出一位真性情的作家波拉尼奥,一部“碎片化自传”。如同他的小说作品,甚至比小说来得更加直观:他以他独特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而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是他唯一的媒介,读者会明白,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苛刻的、不妥协的文学理想。
《纽约时报》的书评则更切中该书的要害:它“并不像是与杰出的波拉尼奥先生一起在开空调的房间里开研讨会,而像是在酒吧里,坐在他旁边的高脚凳上,唱机播放着弗拉门戈乐曲,他喝完了托盘上的皮斯科酒,在你翻开第一页前,不妨给自己也调一杯”。他提醒我们:“与死亡相反,文学活在风霜雨雪中,是无依无靠的,是远离各种各样的政令与法则的,它只遵循文学自身的法则,这种法则只有最最优秀的人才有能力打破。”
“80后”拉美作家笔下“神奇的现实”
正如我们无法在拉美“文学爆炸”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中彻底划清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我们亦无法在本哈明·拉巴图特的新作《理性的疯狂梦》中分辨现实与虚构,甚至无法界定这部新作的体裁。
1933年,纳粹当权的德国,爱因斯坦的好友、奥地利物理学家保罗·埃伦费斯特在枪杀儿子后自杀;1957年,冯·诺依曼去世,他始创第一台现代计算机,确立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参与研制原子弹,出版《博弈论与经济行为》,预见了数字生活、自复制机器、人工智能和技术奇点的到来;2016年,韩国围棋圣手李世石对阵“阿尔法狗”五局,仅惊险赢下一局,这一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而正是在这些确实的历史事件中,本哈明·拉巴图特再度展开了他的想象以及虚构的能力。编者勉强将其归类为富于哲学思考的历史小说,一部黑暗、诡异、充满奇异之美的作品。
2022年,《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的中文版面世时,读者已经从中领略了这位智利作家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展开的对于这个疯狂世界的讲述,五位天才科学巨匠+超人的故事,像是对历史的追忆,实则是对科学与道德,天才与疯狂之间界限的哲学追问。本哈明·拉巴图特据此成为当年文学出版界的一匹黑马。而这一次,他故计重施,高清还原数学家、博弈论学家、原子弹研发人、人工智能之父冯·诺依曼等科学巨匠惊心动魄的一生,在书中,他借人物之口讲道:“如果你知道自己会输,那么继续下残局就没意义了,对吧?”他亦提出这个人类之于世界和宇宙的运行规律:“如果你在自然中发现了某种不和谐,完全否定自然秩序的某种存在,你永远不该说出来,甚至都不要对自己说,而是应该想尽办法把它从你的思想中剔除,肃清你的记忆,小心自己的言辞,甚至警惕自己做的梦,以免神灵的震怒殃及了你。保护自然的和谐高于万事万物,因为它比巨人还古老,比先知还睿智,比奥林巴斯山还庄严,跟赋予这个和其他所有世界活力的生命之源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哪怕是承认无理数的可能、认可不和谐,都会把现实的组成置于危险之中,因为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还有这座宇宙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虚无缥缈的, 都取决于把一切约束在一起的隐形脉络……”
在“80后”拉美作家笔下,“文学爆炸”中曾经震撼读者的“神奇的现实”,已经演进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升级版“神奇的现实”,而作家试图告诉我们,文学永远不会脱离时代与现实而存在,它只是被转化为作家们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罢了。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