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彤
我很少写诗,也没有专门研究过现代诗。以前学习古典文学,读了一些古典诗歌以及诗话,喜欢苏轼,有一年趁“双十一”买了他的全集,不过到现在也没有读多少。
但是做编辑免不了得读诗歌作品,我也偶尔编辑过几位著名诗人的作品。有一次徐敬亚老师给了一组作品,说起来也是神奇,虽然那些语句其貌不扬,校对过三遍后,却像长了脚一样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这是迫使我认真地考虑语言的内在韵律,我想起从前读书时选过一门诗学的课,著名诗人骆寒超教授用他那难懂的诸暨话讲诗学的理论,我翻出当年的听课笔记,边看边琢磨,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理论与实践以这样一种方式碰面了。
2019年,我去山东省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习,同学中有一位来自重庆的诗人,获得过《人民文学》奖,颇受关注。我发现他正在用一款名为“墨迹”的软件写诗,几乎每天都写一首,发在朋友圈里。几位同学都觉得这个软件好用,纷纷下载了,我也凑了一个热闹,从那时起,我也偶尔写几句诗,发在朋友圈,有时会引起许多朋友点赞。我有一位只见过一面的朋友,是陕西一所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她的小说和散文都写得好,我们也经常会在微信上聊一聊文学,她认为我平时记录生活,随手写下的文字很有趣,也鼓励我好好写作。有一天,我发了一首诗在朋友圈,她突然发来微信,说你的朋友圈很逗,可是,你能不能不写诗了呀?她说,你写的那叫啥玩意儿啊。
她的这一说法对我的创作热情形成了一定的打击,我也想起来,关于写诗这件事,我其实也有一些经历。
少年人没有不爱诗的,小时候我们都读过汪国真、席慕蓉,有一年二姐还从《语文报》上邮购了纪宇老师的《风流歌》。高中时我参加过学校的诗歌比赛,我写了一首诗,只有四个字,得了一等奖。诗的名字叫《青春》:“雾/抑或/火”。这当然是因为知道北岛有首一个字的诗《生活》:网。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我从小就很擅长,那次得到的奖品是一本席慕蓉诗集,这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本诗集。当时家里还有两册诗集,一本是惠特曼的《我在梦里梦见》,一本是聂鲁达《诗与颂歌》。那时我完全看不懂诗中含义,只模糊地记得,聂鲁达的诗里,有腹部的玫瑰、胸脯的杯子这种充满了诱惑的句子。这两本诗集的定价都只有一块多,长久地放在书架边缘处,它们是64开的,非常之小,时间久了,封面上的塑料膜还起了泡。它们的译者都大大有名,有袁水拍、楚图南和屠岸,我后来经常在图书馆的书脊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与少年时的感受全然不同。
大学时我也写过一次诗,是在“办公自动化”的课堂上。这门课主要讲如何使用电脑处理文件,30年前Windows还是稀罕玩意儿,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如何在没有鼠标的情况下操作这个系统。这可逗极了,既然有了Windows为何会没有鼠标呢?据说是因为当时鼠标里的那个橡胶球产能不足。在这样一门课上,我与小史同学开始了唱和,你写一首诗,我写一首诗,在课堂上把几张稿纸正反面写得满满的。我给它们取名《波亚涅之什》,波亚涅,pioneer(先锋)地硬译,这个名字颇有一点五四风。大学毕业时,小史同学把这几首诗工整地抄了一遍,送给我作为毕业留念,我一直认真地保存着,可是近来想找却遍寻不见。小史同学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现在也很少见面了。她也还记得我们合作写的那些诗,不过真的很惭愧,我最近几年想起来就翻找,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随着我做文学编辑时间的增加,与诗人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参加诗人们的新书分享会,听了他们的精彩发言,也趁热买了几本诗集。现在我每天都会读一两首现代诗,这在以往从未有过。前不久我的一位大学老师问我有没有写过诗,他在编辑一本诗歌丛刊,如果我有诗歌作品,可以给他投稿。我整理了一组用“墨迹”写的诗发给他,他编发在《星河》诗丛中,我也加入了一个《星河》的作者群,群里的成员似乎大都是大学中文系或外文系的老师。后来我把这组诗编到了微信公众号里。这是我唯一一次发表诗歌,此前也不太想拿给熟悉的朋友们看。记得有一年我听《扬子江诗刊》的主编胡弦老师讲过一堂课,他说,诗歌就是别人突然进到你的屋子时,你放到抽屉里的东西。现在,我把我的抽屉打开了,让朋友们随便看。我想,诗酒趁年华,既然抽屉里有这么几行诗,拿出来又有啥不好意思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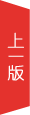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