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六十一中 初三 卯潘越
林奶奶年过六旬,头发灰白,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每日晨起,总会穿一身花花绿绿的戏服,勾眼眉、描红唇,满头扎起精雕细镂的头饰,只为在广场上“咿呀咿呀”地唱一曲秦腔。姥姥告诉我,林奶奶有两套戏服,一套常穿,另一套宝贵得很,被仔仔细细叠好装进一个古旧的雕花木箱里。
姥姥喜听秦腔,天没全亮,就提溜个马扎,听林奶奶的戏去了。我起得早,也便跟着去撒欢儿。广场紧挨着林子,夏天时,草丛中有棱角分明、一蹦老高的尖头绿蚂蚱,还有长约二寸、一身硬黑铁甲的独角仙,以及钻进狗毛里把狗叮得打滚狂吠的狗蝇……诸多昆虫代替电子玩具成了我的玩伴。而秦腔那悠远绵长、壮阔苍劲的调子,也成了萦绕在我心头的梦。
林奶奶唱旦角,端着手,垂着头,水上漂似的倒走碎步。不经意间猛一转身,扬头展眉,提起喉咙,穿金裂石地唱一嗓子,炸雷般地荡开,让我四肢百骸都为之一震。一嗓子过去,他老伴儿打起枣木梆子伴奏,她也放开嗓子唱起来,拖着长腔、带着方言,在百十步之外还恍若有人附耳长歌呢。
林奶奶本是陕西人,某戏班里的角儿,不知怎的搬来了我们这儿。初到时,她爱吃牛肉泡馍、喝白酒、吃辣子。过了两年,林奶奶就像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了,啃馒头吃大酱,煎饼卷大葱,偏偏把唱秦腔这习惯保持下来。
林奶奶说,在陕西乡下,没人不会唱秦腔。白事儿,唱段儿悲怆的秦腔;红事儿,唱段儿豪放的秦腔。遇着什么大磨大难,或者家长里短的破事儿,对着黄土吼上几嗓子,也就安下心了。她顿了片刻,似乎有些哽咽,一字一句地讲:“我虽跟孩子来了这儿,但不能忘了本、没了根啊。”
一年前,林奶奶不知怎么摔了一跤,随后住进了医院。那嘹亮的秦腔,我再也没有听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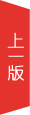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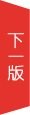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