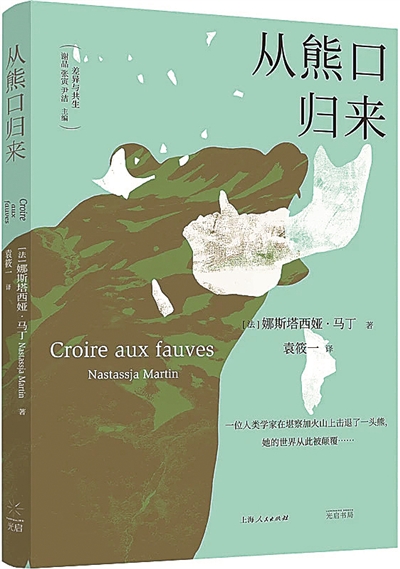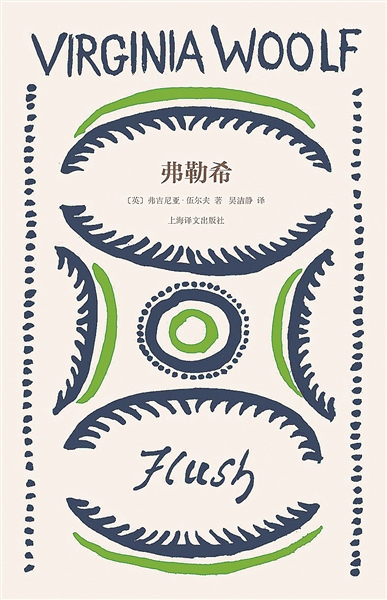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一辆载着上百只毛绒玩具的屠宰场运输车,在纽约大街小巷穿行,车中动物玩偶拥挤着透过围栏,一路发出哀嚎和冲撞声——英国艺术家班克斯10年前的作品《羔羊的警报》,最近作为热门短视频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视频中见此情景的成年人大都一笑而过,孩子们却异常惊惧,甚至和那些动物玩偶一样哭嚎……艺术以假乱真,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而或许只有最纯真的灵魂才能看到貌似荒诞表象背后的严肃设问——
我们真的了解动物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曾写下小说“藏獒三部曲”、最近又有讲述云南象族与人族共生故事的新长篇《大象》面世的作家杨志军一语中的:“动物对人的了解,远比人对动物的了解要多,动物有时候也在研究人类,指导人类。”《大象》中,“缅桂花”家族的象群最终为保护人类和雨林做出牺牲,悲情结局惨烈到让人不适,但杨志军众生平等的生命观一以贯之,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人类中心主义”,只有“生命中心主义”,而“生命”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动物,甚至野生动物。
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在《森林如何思考》一书中,呼吁将人类学作为“思想永久地去殖民化”的实践,他说,我们经常在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属性加诸非人类的属性之上,还自恋地要求这些非人类能够为我们提供出对我们自身正确的反思。而实际上,生命和思想是一体的,无论多么原始多么转瞬即逝,有生命就有思想的存在,哪里有“活的思想”,哪里就有一个“自我(self)”,因此,世界是“有灵的(animate)”,“我们”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我们”。
在《那猫那人那城》中,讲述街猫真实故事的作家朱天心,言辞中也暗含着一种超越差异的逻辑,描述着一种相互共有的形式:“何以要在人的故事、受侮辱的人的故事都来不及说的时候,这样巨细靡遗地写街猫的故事?我想,可能是极简单的一个心情:我不愿意,我不相信,它们的来此世此城一场,是无意义、如草芥如垃圾的,是老天的无聊恶戏……我目睹过它们,认真地在这人族占尽资源的城市艰难生存的模样,我都看到了,跟我们人族一样,没有一只是可被取代、该被抹消的。”
我们应该如何让来自非人类世界之中的思维,解放我们自身的思想?人在一个处于超越“我们”的世界之中意味着什么?这是动物给予我们的思考,是“他者”给予主观唯一的“我们”摆脱惯性思维的路径。
像文学家那样,
感知人与动物的彼此和谐
或许以文学作为方法,来理解人与动物关系,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不妨从一位自然文学作家开始。
19世纪中叶,杰出的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在家乡卡茨基尔山生活,他垂钓、观鸟,与毛茸茸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主张“每个人在附近可触及和熟悉的事物中寻找“伟大”。这位“带着双筒望远镜的诗人”、“走向大自然的向导”,在《雪夜,狐狸毛茸茸》一书中记录了山间生活时与动物之间发生的趣事。
社恐的花栗鼠独来独往,不会离开巢穴超过一跳的距离;雪夜的红狐使“猎人”都为之震撼而忘记开枪,“感觉当时我其实真的捕到了猎物,而且是最好的那部分,在狐狸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他身上攫取了比皮毛还要珍贵的东西”;“被猎犬追逐时,狐狸通常会领先半英里的距离,根据猎犬的速度来调节自己的速度,偶尔会停顿片刻,分神看看途中的一只小老鼠,或是欣赏风景,抑或倾听猎犬的动静。”“我感觉自己几乎都能看到浑身毛茸茸的他蹲坐在那边洒满月光的山坡上,向我这里俯瞰。在倾听时,也许山谷中的树林后会有一只狐狸回应他,那声音颇契合幽深诡异的冬日群山。”……在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互动中,似乎最能体会,山野生趣,岁月静好。
比巴勒斯晚一些,20世纪初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样至爱动物,她为一只名叫弗勒希的小狗立传。它短暂的一生,不仅让伍尔夫与狗的主人、另一位杰出女性、诗人勃朗宁夫人神交心契,更成就了伍尔夫写作中最特别的一部佳作——《弗勒希》的浅白、诙谐与温暖,对应作家其他作品的天马行空,让人们看到伍尔夫内心柔软纯真的一面。故事结尾,老年的弗勒希在某个午后打盹突然惊醒,疯一般地去找主人,然后在她的脚边安然失去了生息。豆瓣上一位书友因此泪目,就像小说中勃朗宁夫人在诗中所言:“我的泪已干,我知道那是弗勒希/超越惊讶与哀伤,我感谢真正的潘/透过低等动物,带我登上爱的巅峰。”
上海译文新版的《弗勒希》,特别附上了伍尔夫的一篇随笔《记一位忠实的朋友》,她在其中回忆已故的狗友沙格,就像为女性发声那样为动物发声:“我们对待动物,亲昵中也包含某种亵渎,半轻蔑的。我们刻意让一小部分单纯的野生生命移居,让他们在我们身边成长,变得既不单纯,也不再野生。你可能会经常在一只狗的眼睛里看见原始动物的眼神一掠而过,就好像他又变成了一只野狗,年富力强,在荒凉地带里狩猎。我们怎能如此无礼,让这些野生生物替换上我们的天性,而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是模仿?这是文明所犯下的又一种精妙的罪恶,因为我们既不知道自己从纯净的环境中带走了哪些野生灵魂,也不知道我们在训练谁——潘神、仙女或树精——在喝茶时向我们讨一块糖。……”正是在这篇随笔的末尾,伍尔夫说出了那句令所有热爱动物的人类感同身受的至理名言:“狗几乎没有缺点。”
像人类学家那样,
重新理解生命与文明的边界
与文学家感性、温暖的笔触相比,人类学家在解析人与动物关系时,态度明显理性。
法国人类学家娜斯塔西娅·马丁在《从熊口归来》中讲述她在2015年夏天前往堪察加半岛做田野调查时与一头熊的相遇。她被咬去了半边颌骨,经历反复手术与漫长的康复期,迎来了某种被当地人称作“半人半熊”的新生。
与文学家与动物的和谐共处相比,这显然不是某种美好温暖的“奇遇”。然而,作为人类学家,娜斯塔西娅并没有讲述野兽、血盆大口、利齿与惊惧,在对血腥现场的反复回想中,她最想搞清楚的是,那头咬住她又最终放开的熊,在那一瞬间究竟在想些什么……这是对“万物有灵”论的一次全新的迫近,令娜斯塔西娅感到困惑的是,“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别的存在都只缩减为我们自己灵魂的状态?”
书中,娜斯塔西娅讲述当地人对于这次“熊吻”事件的不同认知,在他们眼中,人类学家显然已经变成为传说中的“半人半熊”,她写道:“如果一只熊突然撕下你的部分头颅,你到底有多珍贵或神圣?”人类的傲慢在这里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仿佛这世间不存在一种能对人产生威胁的动物。当我们身处一个人类足迹从未停下步伐的世界,我们还有可能感知到人类之外的意愿、那种不受人控制的意愿吗?当人与自然的边界消失,单维度的“身份”被全然推翻,我们又会如何觉察所谓的生命与文明?
在娜斯塔西娅看来,人类学或许能再一次带我们抵达这些未知之地,这场奇遇提供了某种重新看待自我存在与周遭世界的契机。勇敢的人类学家邀请读者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它既展现了坍塌,让我们发现看似“正常”社会生活里的“异常”,“文明”世界里的“野蛮”,它也代表了一种重建,探索我们与世界相处的其他方式。
《它乡何处》的作者黄宗洁在书中引用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风景画理论”来形容人与动物的复杂边界——“一幅美好的风景画最关注的是和谐的整体布局。风景画要显示出不同物体,在大小比例上要相互协调,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那里却专注于直接需求的人来说,他只会留意整体中的一小部分。风景画显示出距离上的优势,只有处于一定的距离才能观察到整体结构,才能在个体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冷静而富有情感的特定关系。但是,从远处看,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本身与观赏者所看到的和谐并不是一回事。”或许作为体验者而不是欣赏者的人类学家娜斯塔西娅,能够引领我们,寻找到那个生命与环境彼此恰如其分的和谐距离。
像科学哲学家那样,
知己知彼,成为热爱动物的人
我们对于动物的理解,究竟存在哪些成见与误解?人类学家与动物学家在与动物的亲密接触中洞察了人类的偏狭与傲慢之后,能够对问题给予解答的却是哲学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晋出版的《我们问对动物了吗?》中,科学哲学家万仙娜·戴普雷以诙谐的口吻阐述了这一严肃命题。那些发生在动物、研究动物的科学家、养殖者、动物园饲养员、驯兽师身上的有趣或惊人的故事,不仅考问我们对动物的所做、所想乃至“所思”的成见,更让我们重新审视动物行为学的理论立场及由此做出的所谓“科学”解释。
“当着动物的面小便合乎习俗吗?”在这一篇章中,万仙娜引用了哲学先辈斯宾诺莎的话:“没人知道身体能做到什么地步。”她提到多位女性灵长类学家注意到,田野工作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月经的生理节律。当她们在野外与雌性黑猩猩共同生活时,月经周期也变得和猩猩们一样,成了三十五天。书中还援引另一位哲学家唐娜·哈拉维对于灵长类学家、狒狒专家芭芭拉·斯摩丝的田野工作分析:斯摩丝原本要按照自己接受的学术训练去行动,即一步步地接近动物,以便让动物逐渐习惯研究者的在场。而为了避免对动物产生影响,研究者必须表现得像个隐形人,要表现得“像一块毫无反应的石头,以使狒狒最终能自如行事,就像人类信息采集者不在场那样”,而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奏效。
最终哲学家作者得出结论:一切都源于主导研究者的动物观。研究者很难想象动物也会琢磨许多关于他的问题,甚至这些问题有时和他提出的问题一样!人们会问狒狒是否是社会主体,却想不到面对此类行为古怪的奇特生物,狒狒也一定会思考同样的问题——“人类是社会主体吗?”——并显然得出否定的结论。最终,斯摩丝从狒狒那里学会了它们彼此交流的方式,于是狒狒开始向她投来凶恶的目光,示意让她走开。她不再被视为一个需要避开的物,而是一个狒狒可以信任并与之交流的主体,一个示意其离开就会离开、能够与之按照明确规则相处的主体。
哲学家作者还列举了另一位灵长类学家雪莉·斯特鲁姆记录的“使用身体”的另一种方式。她在迫切需要小便时,没有像往常那样刻意躲开狒狒们的视线,而狒狒们也被她发出的声响惊呆了。的确,它们从未见她进食、喝水或睡觉。狒狒固然了解人类,但它们从不与人类靠得很近,估计它们认为人类没有身体上的需求——现在它们发现了真相,得出了某些新结论。后来再次遇到这种情况,它们就再也没有反应了。
在这位哲学家作者看来,斯特鲁姆与狒狒之间建立起了令人惊讶的关系——她让它们意识到,她和它们一样拥有身体。这一发现对狒狒而言可能不是小事。它们并不生活在物质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保持稳定,某一关系稍有变化都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关系,因此,每个狒狒都必须长期不断地处理、再处理这些关系,以建立或恢复联盟之网。所以对于狒狒而言,研究者当着它们的面小便这件看似趣闻的事情或许是个重大事件:这个奇怪的异类个体居然有着与它们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身体。
这一篇章里还有一位动物学家莫瓦特的故事。他在观察狼群,并且越来越受不了被狼群无视的状况,而狼群每天都视若无睹地从他的帐篷前经过。于是莫瓦特开始想办法迫使狼群认可他的存在。他说,那唯有以其狼之道还治其狼。也就是标记一片领地的所有权。“一天夜里,利用狼群外出捕食的机会,他开始行动。他花了一整夜,喝了好几升的茶……到了黎明时分,狼群标记过的每棵树、每个灌木丛和每一团草现在都被他重新标记了。他不安地等待狼群回来。和往常一样,狼群熟视无睹地走过他的帐篷,直到其中一头立定不走,惊奇万状。犹豫了几分钟,这只狼折返回来,坐下,死死盯着莫瓦特,盯得他心里直发毛。极度恐惧之下,莫瓦特决定转身背对它,以向它表明这种凝视违反了最基本的礼仪。于是这只狼开始系统地巡视该区域,并精心地在人类留下的每个标记上留下自己的标记。莫瓦特说,从那一刻起,我的这块飞地就获得了狼的认可。狼和人,从此经常轮流从自己领地的一侧重新标记边界。”
在哲学家那里,这些故事都反映出一种非常相似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主宰的情境中,个体要么学会要求另一物种尊重自己看重的某些东西,要么学会回应另一物种的这种要求。这就是此类科学研究具有非凡且独特魅力的原因。要了解观察的对象,首先要学会认识自己。
最后还要引用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为动物的正义》中的论述,在她看来,全世界的动物都处于困境中,人类支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个地方,从陆地、海洋到天空。任何非人动物都无法逃脱人类的支配。很多时候,这种支配都对动物造成不正当的伤害,无论通过工厂化肉食工业的野蛮虐待,通过偷猎和娱乐性狩猎,通过破坏栖息地,通过污染空气和海洋,还是通过对人们声称喜爱的伴侣动物的忽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负有集体责任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动物中的每一个都在努力追求一种繁兴生活,每一个都有社会性和个体性能力,使其能够在这个给动物带来困难挑战的世界上,争取过上合宜的生活。作者希望读者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打动,从而为正义做出选择,成为热爱动物生命的人。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