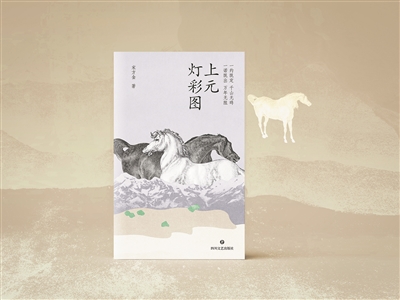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描写明朝中晚期南京元宵节灯市场景的明代画作《上元灯彩图》,价值可与另一幅传世之图《清明上河图》媲美,其久藏于民间,直至2008年公开拍卖,以739.2万元拍出后再度隐入尘烟。没有人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青岛籍作家、编剧宋方金日前面世的小说《上元灯彩图》,便以这幅无名氏的传世古画为引,讲述了一个惊天地、泣神鬼,跨越千年的信义故事。
“历史上的每一张传世之图,都有一个极具张力的结构,是时空漩涡、秘密之眼,也是故事天然的应许之地。”讲一个精彩的好故事,始终是身为编剧的宋方金一以贯之的执念与要务。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度提及故事的重要性。“我觉得很多思想的叙述表达,情感的寄托,都要放在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故事中。所思所想,如何传递给读者,要通过故事来体现,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个有故事的人,往往更容易受到关注。而一个好的故事,总能够承载更加丰富且有分量的东西。”作为编剧,宋方金的小说写作数量不多,2015年,他创作了《清明上河图》,笑谈间,将历史人物重作刻画、勾连,戏谑而犀利。评论家言:其中有每个中国人对历史的疑思和向往,对传奇的致敬与幻想,以及对生活和现实的种种态度。时隔八年,幻想先锋的尝试与现实主义的昭示并未终止,反而愈发强烈。始于传世古画的“图说”,成为宋方金回到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一种独特方式。
传世之图的想象空间
从《清明上河图》到《上元灯彩图》,宋方金为何会选择将传世古画作为自己创作的第一动机?这还要从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的一门写作课练习说起。
那项名为“情景还原”的练习,会让学生自由选取一幅画,或者一张新闻图片,以图中事物为起点,写一个故事,落点还要落在这件作品上。当时宋方金首先想到的是拥有超过八百个人物、情景十分复杂的宋代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后来完成于2015年的小说《清明上河图》,显然是这项练习延续的成果。
在宋方金看来,没有录影设备的古代,图画是古人用于自我表达并留存后世的重要媒介,而古人的寿命相对短,更需要寻找到那些能够彰显矛盾、紧张,具有张力的瞬间和形象来传达情感和信息。因此,传世之图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故事价值。这激发了他书写一个“图说”系列的异趣。一次南京之行给予了新小说创作动力。
那时他应邀赴南京创作一场沉浸式演出,行程中被夫子庙所代表的城市气象吸引,尤其对其中作为古代科举考场的江南贡院印象深刻。正是在相关史料的收集中,他关注到描写南京夫子庙元宵节灯市热闹场景的《上元灯彩图》。专家确认此图可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媲美,然而这位明代画家却并未留名,他因何绘制此图,更无人知晓。这无疑提供给文学写作者更大的自由想象空间。
跨越生死的价值准则
宋方金移花接木,参考了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与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死生交》,把东汉时期张元伯与范巨卿的信诺故事,移至明朝中叶的南京。张元伯保留了原名,范巨卿则化身“孟俊郎”,二人约定一年之后上元灯彩之夜南京夫子庙相见。孟俊郎为履此约,魂行千里;张伯元则抱定“兄为弟亡,我岂能独生”的信义,决绝赴死追随……原先极简的故事框架经由天马行空的细节填充,前情后续犹如一场想象力的雪崩,张元伯父母的爱情、义举与悲壮结局,水鬼聂元伯的前尘往事;老山贼与孟俊郎的交集……突破天地、神鬼的界限,汇聚一部信与义、善与恶的色彩斑斓的志异传奇。
持续三年的疫情所带来的关于现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一系列变故,一直是宋方金在思考的命题。今天,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他坚信,有约必守的契约精神,始终是文明社会的基石,这也成为小说《上元灯彩图》的主题:“一约既定,千山无碍;一诺既出,万年无阻”。回到传统的价值范式与文学叙事:人与人之间最为极致的关系,可以跨越生死,这个世界有比死更具价值的执守与准则。
《上元灯彩图》讲述了一个极致而强烈的故事,它之所以震撼人心,恰恰在于此中人物的“不可为而为之”,“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而作者的用意,也并不只在于一个猎奇的故事,而是它所传达的那些已渐被人们淡忘的文化伦理、民间规则和道德传承,正是它们共同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量子纠缠”。
小说家与编剧的并行不悖
西方有句形容艺术创作的名言:“使造化加速,使神灵放慢。”写作《上元灯彩图》时,宋方金明显感受到了这种介于人神之间的创造快感,体验到来自小说家和编剧双重身份加持的力量。
有关小说写作和剧本写作,不久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中,宋方金恰与导演张艺谋在对谈中涉及。在他看来,小说是线性思维,不管结构如何变幻,从头至尾,是在一条时间线上发展的故事;剧本则是空间思维,镜头的表现力也是空间属性,小说里的千言万语,在电影中可能只需一个镜头就概括了。这也是为什么有小说家认为“总写剧本会把手写坏”。但宋方金更认同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写剧本不但不会把手写坏,反而会使小说写作受益,更具形象感和画面感。创作《上元灯彩图》时,宋方金不但没有放弃小说叙事的绵密深入和对人物心理变化过程由来的探究,更在语言风格上刻意求变。
行文的变化成为宋方金回归古典小说传统的一种尝试。这部以明朝为起点,上下各延宕500年的小说,并没有使用纯粹的白话文写作,而是采用了一种半文半白、相对典雅的书面语言,让读者能够顺畅回到历史性的场景中。
敏锐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作者喜爱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美感,以及富有节奏韵律、主打跳跃性短句的高度提纯的佛经语言的影子。在语言和行文节奏上明确致敬古典的追求,也流露出作者始终不渝的纯文学野心。
保持创造更新的故事载体
美国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说过,“作家总要围绕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为它而生,为它而死?什么样的追求是愚蠢的?正义和真理的意义是什么?过去的几十年中,作家和社会已经就此达成了某种共识,可是在我们的时代却变成了一个在道德和伦理上越来越玩世不恭,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时代,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种价值观的腐蚀带来与之相应的故事的腐蚀。”
这或许正是时至今日全世界都匮乏故事的原因。人们讲不好有关自己人生的非虚构故事,更讲不好虚构的故事。当生产力下降,人们处于迷茫状态时,优秀的故事就不再出现了。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颓废和堕落的时代。这让宋方金更加坚定了讲故事的重要性。他告诉记者,小说创作中,故事性依然是他放在首位的要素。“创作者有责任深入挖掘生活,找出新的见解,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创造出新的故事载体,向一个越来越不可知的世界表达我们的解读。”这是罗伯特·麦基的观点,也是宋方金的态度。
回到这部小说的叙事,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功课,宋方金在极致还原历史细节的真实:江南贡院的号舍,领试卷与找座位的过程,当时人们的交往,酒食,上元灯彩的扎制、描画与售卖……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克制自己的表达欲,不让过多的当代气息对小说的古典意味造成冲击,即便吴承恩的名字出现在小说中,他也是一位正在酝酿惊世名著《西游记》的神游物外的同窗好友,并未突兀于故事之外。这也是宋方金不认同王朔去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起初·纪年》的一个主因: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作家加入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故事讲述者“我”,而正是这个横亘于历史和现实间的巨大的“我”,将所有事物都王朔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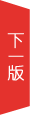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