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藤比吕美

■露易丝·格丽克

■伊莎贝尔·阿连德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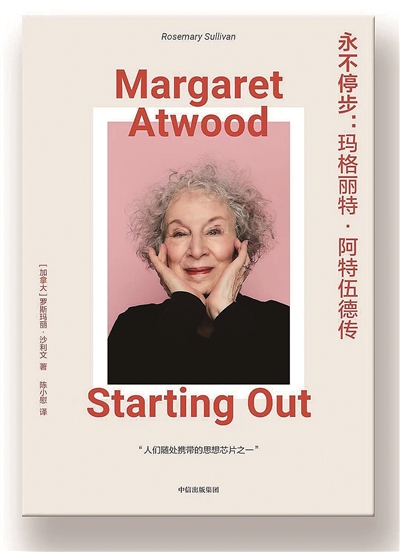
①《永不停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加拿大)罗斯玛丽·沙利文/著 陈小慰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04

②《初老的女人》(日)伊藤比吕美 著 蕾克 译 未读/海峡文艺出版社202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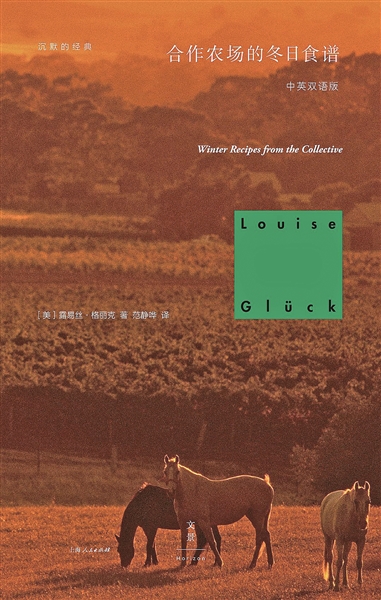
③《合作农场的冬日食谱》(美) 露易丝·格丽克 著 范静哗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04

④《我灵魂里的女性》(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谭薇 译 译林出版社2024.05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露易丝·格丽克有一本旧诗集名称十分醒目——“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这句话出自她一首仿普希金的短诗《预兆》:“我骑马与你相会,梦/像生命之物在我四周聚集而月亮在我右边/跟着我,燃烧。/我骑马回来:一切都已改变/我恋爱的灵魂悲伤不已/而月亮在我左边/无望地跟着我。/我们诗人放任自己/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在沉默中,虚构着只是事件的预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人类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对于诗人格丽克而言,年轻时,那可能只是一场关于爱情的沉迷与想象。而在她生命最后的诗集《合作农场的冬日食谱》中,当那些私密又理性的句子逐渐变得具象、柔和,沉默地虚构出“一棵松树在疾风中摇动/就像人在宇宙中”,此时格丽克所察觉的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似乎才是最真实而又笃定的。程抱一在《说灵魂:致友人的七封信》中说,“灵魂本身就是生命的河谷,在那里,每一个生活过的生命都继续生长和变化。灵魂就像一个从未被勘探过的巨大矿藏,等待我们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开发”。
在程抱一看来,身体—精神—灵魂这三者当中,灵魂才是人存在的根本,远远高于身体与精神。人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发展智力,增长见识,却忽略了倾听灵魂的声音。他不认为人生活在一个“非理性”“无意义”“无意识”甚至“荒诞”的世界,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人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了。既然人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都如此充满灵性,那么我们生命源头的宇宙,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存在毫无意识?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与更广阔的世界联通,就是在勘探灵魂这座巨大的矿藏。
以下我们将认识包括格丽克在内的四位文学女性,她们的一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勘探生命的宝藏,而那宝藏往往随着时间和阅历的累积而历久弥新。正如写信给程抱一的那位友人所感喟的:我直到中年才开始察觉自己的灵魂。在她们的故事中,我们或可自问,人生哪一刻你开始察觉自己的灵魂?
伊莎贝尔·阿连德:
身体老去,灵魂却变得年轻
年近八旬的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感觉自己正在经历“漫长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她,是当代西班牙语世界最畅销的女作家,拉美“文学爆炸”阵营中唯一的女性,小说《幽灵之家》奠定了她在拉美文学界的重要地位。这位迈入耄耋之年,依然热烈地爱、自由地活的女性,用她毕生慢悟,写下《我灵魂里的女性》,她认为,一具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再美好的肉身,依旧可以充满坚定和从容,它们来自灵魂与身体、精神的自洽。
在这本既是碎片化的回忆录,也堪称女性主义宣言的小书中,她记录自己的切身感受:“我的身体在老去,灵魂却变得年轻。我的缺点和优点可能也更为明显。比起从前,如今的我更为挥霍,也更容易分心,但发脾气的次数却少了,我的性格温和了一些。我更加在意一直从事的事业,也更关心我爱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人。我不再畏惧自己的脆弱,因为我不会再将脆弱与软弱混为一谈;我可以张开双臂,打开房门,敞开心扉来生活。我喜欢自己的年龄和女性这一身份,因为正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美国女性主义者,社会与政治活动家)所说,我不必去证实自己身上的阳刚之气。也就是说,我不必表现得坚不可摧。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请求帮助,多愁善感。”
年轻时阿连德也有过大多数年轻女性的困扰与纠结,比如,关于美貌,她一针见血地表示:“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我们的文化都聚焦在年轻、美貌和成就上。对于任何一个女人而言,在这样的文化里保持清醒绝非易事,大多数人都必然迷失其中。”她称自己在人生的前五十年里,始终认为自己就外貌而言毫无魅力,但从年轻到年老,她允许自己始终执着于外表,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让我快乐。虽然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自己关在阁楼里写作,但我喜欢布料、颜色、化妆品和每天早上穿着打扮的过程。”阿连德的母亲有一句至理名言,“没人看到我,可我自己能看到”,她所指的不仅仅是外貌,还有性格和行为等更深的层面。而这也成为阿连德挑战衰老的方式,幸好她有一个真心以待的爱人,给予她极大的帮助,因为在丈夫罗杰眼中,她就是一个个头稍矮的超模。
在阿连德看来,“在经历了绝经,完成了养育儿女的使命后,生活会变得更加简单,不过前提是降低预期,远离怨恨,松弛下来并且认清一个事实,即除了最亲近的人外,没人在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干了什么。不要再为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汲汲营营、装模作样、牢骚满腹或是大发雷霆。要爱自己,并不求回报地爱他人。这是人生中最为宽和的一个阶段。”她在书中用去一半篇幅碎碎念发自灵魂深处的幸福之道:从幼年开始,我唯一的计划就是要养活自己,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其他的路我都是摸索着走过来的。约翰·列依曾说过:“生活就是当你忙于制订其他计划时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人生这条路上,没有地图,也无法回头。我无法决定那些改变了我命运和个性的重大事件,如我父亲的失踪,智利的军事政变,我在海外的流亡,我女儿的去世,《幽灵之家》的成功,我的三个继子染上毒瘾,以及我的两次离婚。或许离婚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但婚姻的成功取决于夫妻双方。
“我的晚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的大脑依然灵活。我喜欢我的大脑。我感觉更为轻盈。我已经不再缺乏安全感,我摆脱了不理智的欲望,种种毫无益处的心理情结,还有其他不值得犯下的罪过。我慢慢地放手,慢慢地舍弃……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就连最亲密的家人也各奔东西。紧抓着某人或某物不放是毫无作用的,因为这个宇宙本就趋于离散、无序和混乱,而不是聚合。我选择了一种简单的生活,少一些物质的东西,多一点闲暇的时间;少一些担忧,多一点消遣;少一些社会活动,多一点真正的朋友;少一些喧嚣,多一点寂静。”这是阿连德给予每个人的箴言,不仅仅对于女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人生没有预设,只有不断打破的规则
在加拿大作家罗斯玛丽·沙利文笔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写下著名《使女的故事》的锋芒毕露,文字黑暗、消极、厌世的女作家,而是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具体的人。
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六个月大时她就被放在背包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丛林生活。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吉姆·波尔克说:“她是名副其实的丛林之子。”作为当下最有世界影响力的加拿大作家之一,阿特伍德出生的那个时代,女孩们会因为创作野心而受到打压。但她却坚信自己要写诗,要成为作家,或许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灵魂——“丛林之子”注定要打破时代的桎梏,开启以写作为终极理想的探险历程。无论是在“波希米亚使馆”参加文学活动,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还是在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做小职员,她都堪称一颗闪亮的文学明星。
《永不停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这本传记中描述了阿特伍德在一众厌女严重、不可一世的男文青中朗诵她的诗作的情景,描述者是对阿特伍德怀有敌意的欧文·莱顿的妻子阿维娃。那是在1969年,阿特伍德30岁时,“阿维娃记得,当她第一次见到阿特伍德,简直被她的美貌惊呆了,她穿着一件黑色天鹅绒连衣裙,头发柔顺,皮肤如瓷器般光滑,看起来就像拉斐尔前派作品中的女主角。(阿特伍德一定很是沉迷于对表演服装的热爱。)莱顿一看见她,就感到气不打一处来。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第一次参加她的诗歌朗诵时,她在台上朗诵,莱顿就特意在观众席上大声读自己写的诗,然后很快睡着,鼾声大作。但阿维娃说,阿特伍德似乎并不受其影响。”而身处特定时代的玛格丽特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般自信。当时的她曾为自己设定了如下女性作家的生活场景:除了阁楼和肺结核,还有神秘和孤独的元素,比如穿着黑衣服,学会抽烟……她写道:“我读了她们(女作家们)的传记,读后感到沮丧且扫兴。简·奥斯丁始终没有嫁给达西先生。艾米丽·勃朗特英年早逝,夏洛特·勃朗特死于难产。乔治·爱略特从未有过孩子,还因为与已婚男人同居而遭世人排斥。艾米莉·狄金森东躲西藏……也有些人成功地将写作与我所认为的正常生活完美结合起来,但众所周知她们并非一流作家。我的选择一方面是卓越与厄运,另一方面是平庸与安逸。于是我咬紧牙关,迎风而上,放弃了浪漫真爱,戴着角框眼镜,板起脸来,以免被误认为是个胸中无一物的肤浅之人。”
绝不机械地依照规则而活,阿特伍德的人生也许一直都在贯彻这个信念。就如同传记开篇所讲述的,在她小时候观看电影《红菱艳》时的感受一样,那个从高处纵身跃下的身影,足以令灵魂震动觉醒。而正当公共生活风生水起之时,阿特伍德却与丈夫吉布森搬到了有鬼魂传说的小镇穆尔穆,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生活与父母曾给她设定的“一同在后院扫落叶模式”非常接近。这里独特的乡村生活也给予她写作新的养分。相较于之前的迷茫,她曾在年近不惑时表示,“我曾以为我错过了其他女人拥有的许多东西——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孩子,没有丈夫。现在我知道我可能什么都没错过。”《纽约时报》评价小说《浮现》的一段话也可用于对阿特伍德人生的总结:“阿特伍德否定了爱默生的格言,即生活的真正艺术是在世界的表面滑行自如,她向我们展示了,倘若人想要在今天过一种自省的生活,就必须去探索其深度。”
伊藤比吕美:
变老意味着全新的自由
伊莎贝尔·阿连德说,她拒绝那种一人一狗的悲催人生,而伊藤比吕美的个人生活正是由一人、一狗和许多许多盆栽组成。62岁的日本女诗人伊藤比吕美,在送走双亲和丈夫后,开启了被她称作“初老”年纪的独居生活。她带着小狗克莱默离开美国,重回日本,在不断的别离中,直面生命的荒芜。“现在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了,我真的自由了。”
伊藤比吕美曾在《闭经记》中分享女性在闭经前后的生理和心理变化:育儿、孩子独立、照护、夫妻关系……满身疮痍地像狮子一样战斗的姿态,确实是一部与人生格斗的女性战记。如今的伊藤,在《初老的女人》中又以敏感坦率的笔触写下一个女人老后的身体和精神变化,以及一个人生活的自由和寂寥。
伊藤本人拥有一段相对传奇的人生,20岁患厌食症,35岁患忧郁症,离过婚,40多岁去美国生活,55岁和美国画家同居,有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大女儿未婚先孕,伊藤潇洒地当了外婆。在父亲去世前,她每个月长途往返于美国加州和日本熊本,父亲去世后,每天跳“尊巴”,瘦了4公斤,重新穿回牛仔裤。
她在新书中记录琐碎的生活和感悟:“人之老去,就得忍受这种寂寞,没办法。这道理我懂。人不仅要寂寞地老去,还要寂寞地独自死去。我父亲就是。现在我越寂寞,越感觉自己是在赎罪。”“前几天晚上下着冷雨,我带着沉重的行李到达东京时,已经精疲力竭。……六十三岁的老奶奶在冷雨里抱着大行李,白发凌乱纷飞,恳求司机快点儿载我,司机却躲避了我的视线,只一个劲儿地摆手示意我往前。冰冷酷寒的东京冬夜啊。”“‘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这是石垣凛《那一夜》诗中的一句,……也是我每天的心声。……咳嗽还没停。咳到痊愈时才会停。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这场病简直就是缩写的‘活着’,中心思想就是‘一直到死,都得活着’。”
露易丝·格丽克:
接受生命的衰败就如同接受冬日的艰难
2020年,以精确、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对孤独、家庭关系和死亡的洞察力著称的美国桂冠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也让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16位女性获奖人。
一直以来,格丽克拒绝人们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对照连接,而在那些私密而凌厉的诗篇中,我们却总能找到她具体的生活的影子。在《合作农场的冬日食谱》露易丝·格丽克生前最后一部诗集中,作品的意象更加具象,常常是某个具体场景的描摹与延展,在生命走向终结之时,她开始回顾并思考自己的一生,淬炼诸多复杂的人生经验,审视人的存在中根本性的孤独。
此前,格丽克曾回忆她的厌食症,“到青春期中段,我发展出一种症状,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一开始她自认为是一种能完美控制结束的行动,结果却造成了一种自我摧残。十六岁的时候,她认识到自己正走向死亡,于是在高中临近毕业时开始看心理医生,她将看病的过程看作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瘫痪转化为一种洞察力。而这种能力,在格丽克看来,于诗歌创作大有益处:“我相信,我同样是在学习怎样写诗: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选择深层的东西。”那些观照个体心灵的成长与变化的人注定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
当诗人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她在诗中展现了弥漫着清冷的冬日气氛,格丽克一次次辨认,在荒凉的景象里生活的艰难,但这时更需要耐心、灵感与对抗孤独和衰老的特殊技艺——诗人写道:“本书只收录/冬日食谱,这季节生活艰难。春天时/谁都能做一顿美餐。”她已经做好了迎接终结的准备,体验生命的衰败就如同接受冬日的艰难,如同这首诗所写——最漂亮的苔藓会被留着/用于盆栽,放在/一个专门的小房间/不过我们没什么人有这方面的天分/即便有,也得经过/漫长的学徒期,而规则又很繁杂/一道亮光照在正被修剪的样品上/……/在我看来,树挺漂亮/也许还没修剪完成,但已很漂亮/它的根须披着苔藓——我不可以/动剪刀修,但我手捧着盆子/一棵松树在疾风中摇动/就像人在宇宙中。
这是一部凝集格丽克一生经验的、散发清冷之美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