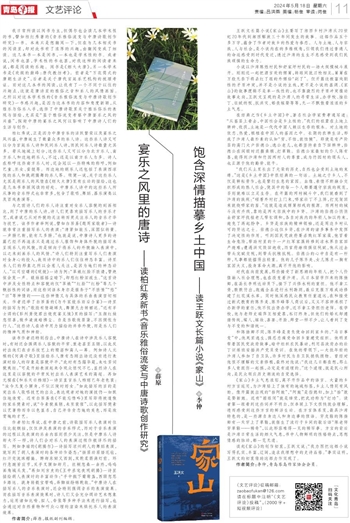李仲
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主要写了湘西乡村沙湾从20世纪20年代到湘西解放三十年间发生的故事。这部作品五十多万字,蕴含了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人与土地、人与宗族、人与社会,是小说内在的多维视角,引领我们透过普通人的命运感受到时代变迁,透过沙湾的生生不息感受到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小说以沙湾陈姓村民和舒家坪村民的一场大规模械斗展开。刚刚还一起把酒言欢的甥舅,转眼间就刀枪相见,舅舅在万般无奈下将杀红了眼的外甥给“剁了”。但开篇这极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并不是小说的主线,更不是小说的基调。《家山》的叙事逻辑不是单一线性的,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推动故事走向,王跃文呈现的是沙湾人的寻常生活,办学校、抽壮丁、征赋纳税、抗洪灾、婚丧嫁娶等等,无一不飘散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在经典之作《乡土中国》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祖辈在土地上耕种、收获,土地是一代代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对土地的依恋、热爱,根植在中国人的基因之中。长期的农耕生活,形成了沙湾人最朴素的认知“穷,不怕,就怕懒”。即使是有产阶层的高门大户佑德公、逸公老儿,也都坚持亲自下田耕种,佑德公在闲暇时还箍粪桶、打草鞋。佑德公家最初的仆人陈有喜,能得到沙湾和竹园两村人的尊重,成为竹园村的领头人,也正源于他的勤劳、能干。
“我们从土里长出了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这是《乡土中国》中很经典的一句话。土地之于乡人,不仅是耕耘劳作,也是繁衍生息的家园。血缘、亲情不断融合交织形成的熟人社会,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宗族的规范,否则就难以立足生存。在开篇的两村械斗中,我们就看到了沙湾的族规:“碰着外村打上门来,哪家壮丁不上阵,打完架回来就烧哪家的屋。”这就是造成甥舅相残的根源。而两村的械斗没有升级,靠的是两大宗族中的乡贤。沙湾的佑德公悄悄去舒家坪找桂老儿帮忙调和,各自对族内的年轻人加以约束,避免了再起纷争。乡贤是宗族的精神领袖,还是周边乡村认可的贤达之士。佑德公这位乡贤,在沙湾的诸多事务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听到国民党政府要杀戮红军家属,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村里的十一户红军家属转移到凉水界自家田产避难;遭遇洪灾毁田绝收,而官府继续强征税赋,他从过去带头完赋交税,到带头抗粮抗税。佑德公的心中自是有一杆秤,凡事都能掂得出轻重。他的儿子陈齐美、女儿陈贞一胸有家国大义,投身革命大潮,离不开他的影响。
时代在向前发展,那些接受了新思潮的年轻人,把个人价值融入社会理想,也在改变着沙湾。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扬卿,在县长李明达动员下,接下了兴修水利的重担。他不拿工资,默默付出,跑遍全县进行水利勘测,最后克服万难成功修建了红花溪水库。同时他深感民众教育任重道远,在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陈齐美、陈齐峰等人商议后,又义不容辞承担了办新学的重任,他不仅出资办学,还不拿工资担任老师。在学校,他与老师史瑞萍互相爱慕,私订终身,但他们的婚礼却遵循传统,媒人、嫁妆、喜宴、开脸、拜堂一样不少,让人看到了变与不变的和谐统一。
和陈扬卿不同,陈齐峰是肩负使命回到家乡的。“马日事变”中,他死里逃生,强忍悲痛受命回乡重建党组织。他明里帮着国民党政府做事,暗中组织农民暴动,利用县政府办的壮丁训练班安插共产党员受训。在他的带领下,一大批年轻的沙湾人参加了自卫队,许多村民为自卫队捐钱捐物。曾经对他很不理解的父亲修根,最终对他说:“我这几日都在想,那么多人肯跟你一起搞,必定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民心所向,是民众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选择。
《家山》乡土气息浓郁,离不开作品中的语言。大量的乡村方言运用,为沙湾贴上了独有的地域标签,乡土人情别有风韵。像开篇就出现的“抬阿娘”,“阿娘”是指媳妇,加上“抬”就是娶新娘。还有“困眼闭”就是睡觉,把武功称为“打功”。读者第一眼看到这些词并不明白,但串联上下文很快就会理解,进而感受到这些方言的鲜活生动。在方言体系里,最具沙湾特色的,是一些源自身边人和身边事的俚语。穿皮鞋的陈扬卿有一天穿上了草鞋,就催生了流行于乡间的歇后语“陈老师穿草鞋——稀奇”,以此形容难得一见的稀罕事。方言的背后是沙湾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书中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思想情感的脉动,都一览无遗。
谈起《家山》的创作初衷,王跃文说:“我力图把这部小说写得扎实、丰富、辽阔,追求我理想中的史诗品格。”事实证明,王跃文的初衷借助这部力作实现了。
作者简介:李仲,青岛琴岛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