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
最早读德国诗人海涅《宣告》中的诗句,他笔下的波浪之美让我难忘:暮色朦胧地走近,潮水变得更狂暴,我坐在岸边观看,波浪雪白的舞蹈……海涅年轻时爱上了自己的表妹,但表妹后来却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失败的爱情在他心里留下了悲伤情感。海涅在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去北海的诺得奈岛散心,并在那里写下了《北海》组诗,这是其中一首。
某年中秋,我在帆船基地看黄海的中秋之月。那时奥运帆船赛刚过去,帆船静静停在泊位上,桅杆倒映在海水里。我们到达海边时,一些摄影爱好者已架好相机,他们是来拍海上圆月的。黄海的波浪从远处涌来,带来阵阵涛声,海是暗蓝色的,附近的灯光也是暗蓝色的。一会儿,一轮圆月从海面慢慢升起,月亮下半部分湿漉漉的,仿佛沾满海水,海面渐渐明亮起来。一艘货轮从月亮升起的海面驶过,海水轻轻波动着。月亮越升越高,海面落满了月光。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海上生明月。”
在对城市的理解中,我更喜欢港口城市。斑驳的客轮、暖暖的汽笛、从窗口即可望见宽阔水面上低飞的水鸟。港口使城市动静结合,不停来去的客轮使情感添了些离愁、牵动与怀念。很早去上海时曾坐过一次客轮。那艘客轮有些旧了,船体锈迹斑驳。大概因为雨季,甲板新刷了油漆,有一股刺鼻气味。我在北方长大,平时都是坐火车出行,很少有机会坐船,脚踏在甲板上,觉得天摇地晃。不久,船舱坐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顿时四周一阵嘈杂。随后,船尾传来柴油机低沉的轰鸣声,客轮慢慢离开码头,岸边的建筑仿佛默片镜头,从灰色背景下渐渐隐去,当时意识里出现了瞬间的混乱,分不清是建筑在后退,还是船在前行?汽笛在雾气中“呜呜”叫着,心中陡生一种茫然。客轮进入大海时方才懂得什么叫沧海茫茫,什么叫孤旅无涯。在落日即将没入海面时,大海被夕阳染成火红的颜色,突然感觉生命的悲壮与美丽,那个意象一直留在心里。太阳照在甲板上,光线逐渐减弱。一群海鸟逆风飞来,它们在海面变换着队形,仿佛移动的星座,它们不断把叫声撒落在寂静的大海里。
海洋美丽而辽阔,同时也充满未知。当年,我的工作单位与海只隔一条路,夏天午饭后,常和同事在办公室换上游衣,一起往海边走去,我们沿岸边的石阶进入海水。海面漂着一团团褐色水沫、渔网的浮标和漂流瓶,还有丝絮般的海草。几只伞状水母在海上游动,游泳必须躲开这些看起来漂亮的水母,因为它们分泌一种微毒的液体,对人体有害。有一次,我从浅水往深处游去,当游过“鲨鱼网”后,发生身边人越来越少,海蓝得使人恐慌。一只大水母朝我游来,我往四处看去时,发现周围有许多水母在游动,一种恐怖突然袭来。我转身快速往岸边游去。
这座城市有一个特别群体——海员,我一直把他们叫“水手,”水手在船上是等级最低的海员,平时负责甲板清洁保养,包括敲打船锈、上油漆和船靠岸时调整缆绳等杂活。我有一个水手朋友,他经常随船往来于东南亚沿海国家,他在船上见到过鲸鱼列队从海上游过,他喜欢大海和航行,他无数次经历海上的风暴。
我小时候喜欢口琴。放学后,常在路口听一个师傅吹口琴。那个师傅是个配钥匙的,四十多岁,阔脸膛,两只眼睛有些忧郁。他每天在路口摆开一个工具箱,坐在马扎上给人配钥匙。他有一双灵巧的手,不光会配钥匙,还会修伞、修拉锁、修手提包、修钢笔,重要的是他会吹口琴。平常,师傅没事时就掏出一只口琴,在街头轻声吹着。一次,师傅吹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听着,觉得自己随着口琴声来到一片海上。那时我很想有一只口琴,但却买不起。一次,那个水手朋友出海前送给我一只口琴,那是一只“布鲁斯”口琴,是他在一个欧洲港口买的。在欧美国家,人们称“布鲁斯”口琴为民谣或蓝调口琴,那只口琴有十个琴孔,音色纯美中略带忧郁。
一年夏天,那个朋友出海再没回来,他最终被风暴留在了海上。 他去世那天,我一个人在礁石上看海。那也是一个初夏,海面上雾气初现,海水正蓝。望着波浪从远处涌来,突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伤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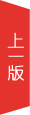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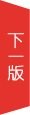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