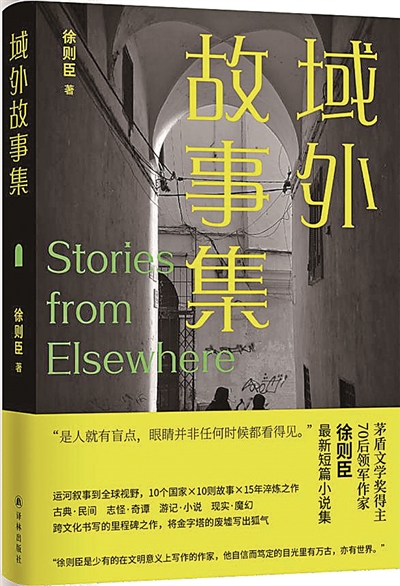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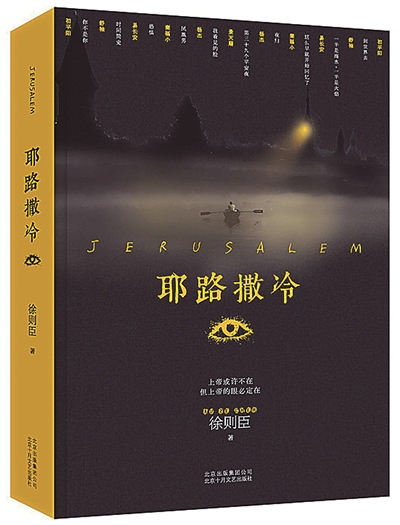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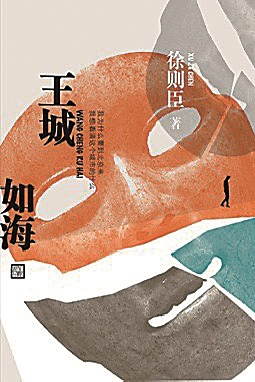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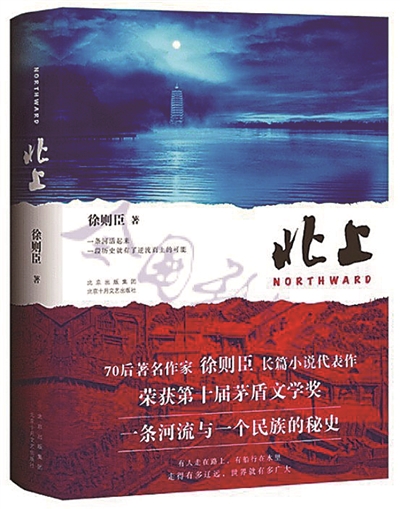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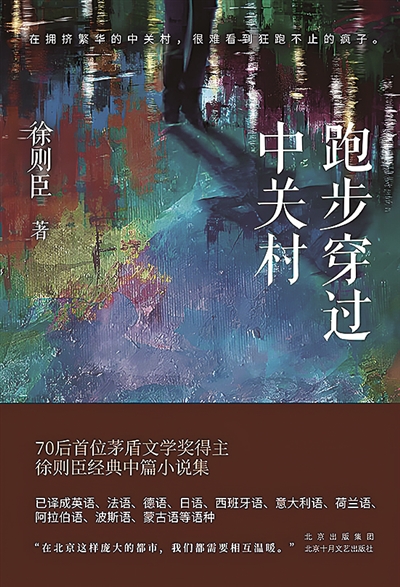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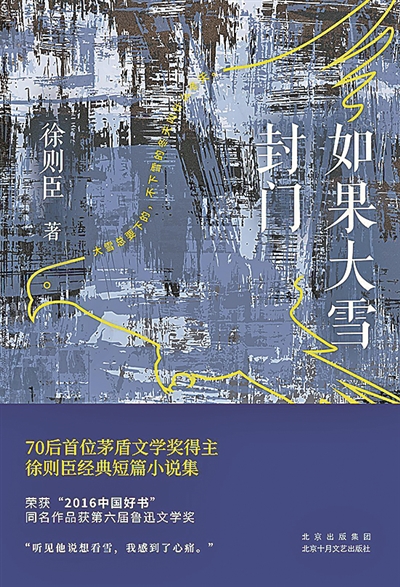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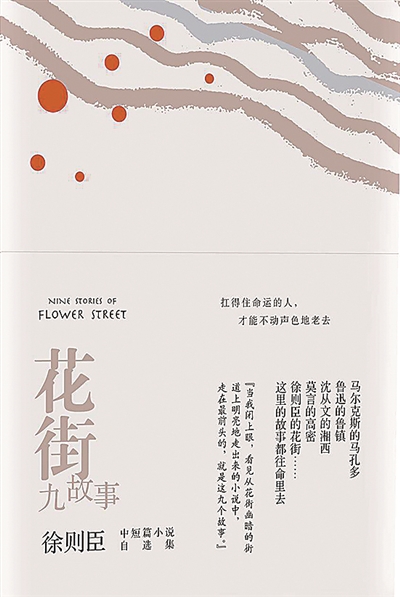
徐则臣小说书单
《域外故事集》
译林出版社2025.08
《如果大雪封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版
《耶路撒冷》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版
《北上》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版
《王城如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
《花街九故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版
《跑步穿过中关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因电视剧改编引发的热议,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北上》和作家徐则臣重返大众视野。而只有资深的小说读者才会发现,自2019年《北上》折桂茅奖之后,徐则臣的小说创作已开始发生转向——从“大运河叙事”的时空浩瀚,《耶路撒冷》对“70后”一代心灵史的深长探问,《王城如海》的“北漂”孤独沉思,回归架构轻盈的短篇。他甚至尝试了从未涉足的类型小说“鹤顶侦探”系列。不久前,横跨九个国家、由十个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亮相上海书展,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距他的短篇《如果大雪封门》斩获鲁迅文学奖已过去11年。
作为鲜有的集齐“茅奖”、“鲁奖”、老舍文学奖等国内顶级文学奖项的“70后”小说家,徐则臣从未停止探索试新的脚步,而他的尝新,依然从短篇开始。“短篇小说对小说家来说是试验场,也是挑战自己的好文体,你不断压缩篇幅,就会发现写法要变,讲故事的方式要变,最后连‘故事’这个概念都会发生变化。”此前,徐则臣提及自己对短篇小说写作的偏爱,在他看来,短篇是作家锻炼写作能力、不断更新和升级对小说文体理解的绝佳载体,尤其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写作近三十年的老作家,传统的写法和路径已失去意义,他更希望在小说里不断寻求突破,拓展新意。
《域外故事集》在远方展开的叙事,所呈现的拓展有些特别——十个来自不同国度的貌似亲历的故事并非猎奇,却也绝不平淡,作家以白描之笔娓娓道来,戛然而止,亦真亦幻——
雕刻玛雅人面具的长相酷似中国人的手艺人,原来竟是失踪多年的中国亲人,甫一现身又神秘消失在同样不知所踪的金字塔影像里了;南美大陆纵深处的紫晶矿洞里,居然天然勾画出一张熟识的中国男人的脸;一次德国城际之旅,与各国“德漂”邂逅,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曼妙;与哥伦比亚游击队员蒙面诗人惺惺相惜的一面之缘,仿佛是在为超越一切文化与世俗障碍的诗歌正名;白俄罗斯冰河上独自垂钓的中国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似乎并不孤单……
其实小说中的国别并没有那么重要,亦没有所谓异域风情的过多渲染,同样,想要从中读出曲折离奇的读者恐怕也要失望了,作家显然无意于情节的原委,而更致力于讲述方式的非常。如他所言:“我会避开自己已经习惯、已经审美疲劳,甚至厌倦、鄙弃的写作方式,当文体进入平台期,就需要开疆拓土,哪怕是弯路错路,也值得去尝试。”在陌生的远方,有故事的中国人各自演绎着国人似曾相识的新奇,在貌似平淡的“剧情”中,会发现其根植本土的深厚与面向世界的开放,发现那些遥远的陌生背后,未曾尽述的新鲜与突如其来的一丝震撼。
在8000字左右的篇幅里浓缩文化的差异
“在有限的8000字左右的篇幅里,将想讲的一件事情讲清楚”,一种近乎偏执的“写作训练”成就了《域外故事集》的写作缘起。囊括了10个发生在九个不同国度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累积的时间跨度长达15年,中间虽有断续,但作家徐则臣写作它们的初衷从未改变。
2010年从美国访学归来的徐则臣创作了短篇《古斯特城堡》,也就是《域外故事集》里的第一篇,讲述一座古堡“闹鬼”的真相,生动有趣,亦可见不同国度间人们的文化差异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完成这一轻巧短篇之后,作家萌生了书写一个系列的念头。“域外故事集”的短篇名称则源于鲁迅兄弟二人的一部译文集《域外小说集》。
小说的第二篇写于德国之行后,《去波恩》,异域国人的身影以及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异国人士在短篇里交织,互为表里,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意味深长。两篇过后,短篇集的写作意向便被接连到来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三部长篇的创作高潮湮没了。直至新冠疫情期间,才有机会重拾搁置。那段时间亟须开窗透气,一面是现实中的窗,另一面则是内心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窗,远方的故事此时尤其具有吸引力,于是作家重拾去国见闻,真假参半、虚实结合地写就一国一故事。
为什么是一个国家一个故事呢?徐则臣给出答案:想把自己在每一个国家所认识到的风物、人情、地理、人文,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浓缩在一篇小说里。而一国一故事,会让这种感受更强烈。自言在2010年之后已很少写作中短篇的作家,对短篇的创作更显苛刻:他要在8000字左右的篇幅里,把想讲的一件事情讲清楚。
在胡安·鲁尔福的土地上完成蒲松龄式的开场
“有鬼魅之气!”上海书展上,作家阿来说出阅读《域外故事集》的第一印象。而这也正是徐则臣试图在小说中传达的氛围,将《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的传统叙事方式,与异域风物和小说人物结合,融入现代性的故事书写,是徐则臣对抗趋同的文学叙事的差异化表达。
小说集中,《玛雅人面具》一篇尤其神鬼莫测,“我”在墨西哥的一处景区偶遇一位长相酷似中国人的掌握独特面具雕刻技艺的玛雅人,这个名叫胡安的手艺人也成为带“我”去到雨林深处不为人知的古老金字塔的导游,而当“我”的父亲从那独特的雕工中认出这位失散多年的兄弟,胡安,连同那座金字塔,却又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踪迹……
徐则臣有意将在“聊斋”里习得的弥合阴阳两界的穿越之法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引入到不同地域、文化和种族中间,让他们发生碰撞与融合。而他从蒲松龄那里受到的启发,在300年后的玛雅人故地,在另一个叫作胡安·鲁尔福的作家那里得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演绎。在这位墨西哥作家为数不多的中文译作中,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主人公,也在阴阳两界自由穿梭游走,行踪不定。他比“聊斋”里的崂山道士更胜一筹,无需任何咒语,亦无需助跑,既可丝滑穿越时空,据说正是这部小说,启发了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胡安·鲁尔福贡献了现代小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穿越虚实之界的技艺,而蒲松龄比之早300年就完成了这一文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徐则臣的《域外故事集》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极具穿越感的评语——“在胡安·鲁尔福的土地上完成了蒲松龄式的开场”。
一直以来,徐则臣都在践行作家汪曾祺给年轻作家的建议:补两门课,一门是古典文学,一门是民间文学。如阿来所说,《域外故事集》里不仅有“聊斋”的影子,还有如《阅微草堂笔记》的“志怪”气息,它们化身为一种气氛的营造,悬念的设置:那些层出不穷的悬念设置,仿佛马上就要触发情节的转化,却又一晃而过地消解了。往往是情节并没有陷入离奇,而奇异的气氛却已达成。这种奇异的氛围来自对古典叙事资源的传承。
徐则臣尽其所能地接续古典文学的传统,一如他一直所做的,在小说的表现方式、写作方式上务去陈言,在传统的主流文学与类型文学间尝试突破边界,寻求独特。在阿来看来,《域外故事集》充当了一个实验性文本,它表明,今天还有很多作家还在尝试拓展,为表现适当的内容拓展出一种形式空间。这将改变我们某些固有的错误认知,即认为:只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发生文学革命的时代,先锋文学的浪潮过后,今天的作家在写作形式的拓展方面已无所作为。“《域外小说集》正是小说表达形式探索方面的一个实践,过去我们过分地炫技,在外在观念和形式上习惯于直接、间接地照搬外来的东西。而今,即便是关于域外生活的题材,我们的写作方式依然可以回溯中国的传统文学叙事,其中的笔法、气息都有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则臣和这本书做出了一种努力。”
在亦真亦幻的叙事里拓展生活的可能性
《域外故事集》里,《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一篇的讲述方式尤其独特,据说故事的缘起是一次白俄罗斯的冰上散步,第一次感受到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作家的灵感细胞异常活跃,当经过一处湖泊时,湖面的冰层特别厚,冰天雪地中,见一名冰钓者独坐在冰天雪地中,孤独而笃定,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此时的画面,在徐则臣脑海中即是一篇小说不容错失的细节场景。于是,在这篇以孤独冰钓者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作家曾经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中的主人公,从放鸽子的小伙成长为知名画家的林慧聪,意外现身,与这名冰上垂钓的中国人邂逅于陌生的异域,彼此给予一丝未曾言表的默契暖意。而冰钓者最终身死于冰面之下,生命定格于林慧聪的那幅与小说同名的画作之中……现实与故事,亦真亦幻,扑朔迷离,而从小说的叙事结构看,层层铺设的虚实,每一节的人称都在变化,唯有进入最内层视角的读者,才能切实感受到戏剧性的故事内核。
有人试图在小说中寻求一种高深莫测的意义,而对于作家而言,描摹一种极寒的氛围,塑造一个身处极度孤独和贫瘠的情境中的人,如何获得内心片刻的安逸和丰盈,或许即是故事的意义,甚至冰钓者最后的死亡都显得并不那么重要。
小说中的每个故事,都具有真假参半、虚实相间的意味,而能激发读者兴趣的,也恰是这些在虚实之间腾挪的故事,它们令读者沉浸于无限的猜测和遐想中。徐则臣坦言,故事一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甚至是他的亲历。比如《瓦尔帕莱索》中遭遇的吉卜赛女子;《蒙面》一篇中,哥伦比亚游击队员诗人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蒙面朗诵;乌拉圭的《紫晶洞》故事中,的确有连云港东海县的老乡去南美开矿,做紫水晶的生意,的确也有许多人把命丢在了那里……对于小说家而言,正是这些亦真亦幻的叙事,为实际生活增加了无限的可能,并让读者得以想象这些可能性。
在徐则臣看来,所谓小说的技巧,即是以虚构的人物展开真实的日常,并让读者相信其真实性,而不再追问其中人物的真假。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曾经,我们都会为小说开篇主人公变身甲虫的离奇情节感到震惊,但随着叙事的深入,慢慢就不再执着于他为什么变成甲虫,反倒会觉得变成甲虫之后的生活,逻辑严密,经得起推敲。小说的魅力正在于此,足够扎实的细节,能让虚构变为真实,“强劲的虚构产生真实”。
在细节的微妙处呈现宏观的意义
上海书展上,《域外故事集》的新书推介活动设定了一个主题——“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而徐则臣也预判了读者的预判:“很多人可能一听说是把故事放在域外的小说,就会想,是不是在处理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比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说实话,我的确想处理这样一个主题,但在写小说时却并未以此为重点。”在他看来,小说要提供的,是那些细节的微妙之处,“比如:当一个中国人与一个乌拉圭人相遇,举手投足间,二人在细微处的差异,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而我只呈现言行的细节,其他留给读者自己去感受。”
徐则臣讲述写《玛雅人的面具》时的经历,回程前他收集了许多面具,挂在家里,整天盯着面具看,那面具空洞的眼神里突然有一道目光袭来,感觉特别强烈。而这种目光既是一个中国人的目光,也是一个玛雅人的目光,一个墨西哥人的目光。当他把它们写下来,很多读者说,你这是在探讨中国跟拉美文化间的差异性,但在写作时,他便只有实实在在的对于那道目光的感应。
再比如小说集的最后一篇《边境》,讲述边境线上隔着铁丝网和界河的两名跑步者的交集,亦是集子里最悲情和写实的一篇。那张用油纸包好,又封进塑料袋里的一方所在国家的地图,最终成为泅渡溺亡的另一方身体上唯一干爽的东西。没有读者会对这个悲伤的细节无动于衷。而据说,这也是十篇小说中唯一没有写明国别的一篇,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在边境上看到了铁丝网、河流与小路的读者再次想起小说中虚构的故事。隔着铁丝网传递的新球鞋,挂在溺水者的腰间,已磨损得不成样子……无数细节刻画的真实感给予了小说比金句更能共情的力量。
徐则臣据此认为,一个小说家深刻与否,不在于他是否在小说里直白地提供了某些金光闪闪的句子,某个富有哲理的判断,而在于将自己的观念有效融入一个个细节中,融入句子、手势、眼神,甚于一个转身里,让读者体会到那些宏观的意义。“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力图在写作之前有一个抽象论点,但在写作过程中,我会把我那个相对抽象的明确的结论掰碎了,揉开了,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入人物的形象里、故事的细节里,阅读者不论国籍,都能以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生命体验,从不同角度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徐则臣说,短篇写作的困难即在于,让故事赋予作家一个“可阐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物形象具备足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么,一千个读者就能从自身看见一千个哈姆雷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