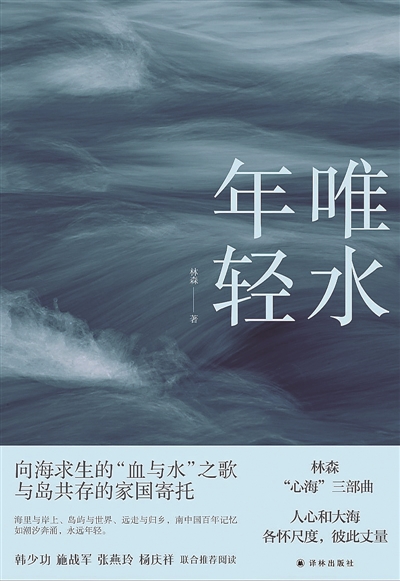
《唯水年轻》 林森 著
译林出版社2024.03

《走仔》 黄守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05

■林棹的《潮汐图》封面(局部)。

《新南方写作》 曾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07

《时间边境》 (马来西亚)贺淑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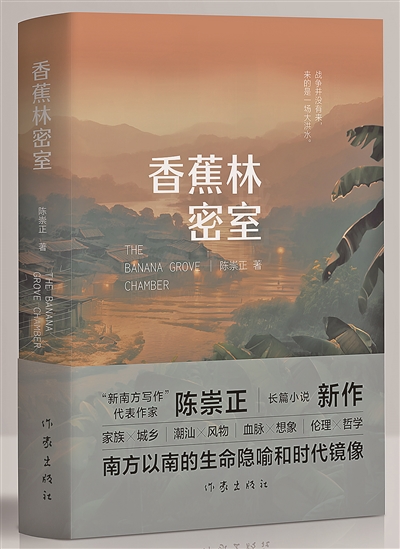
《香蕉林密室》 陈崇正 著
作家出版社2024.04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南方,作为文学地理概念,似乎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古老命题,而华语文学世界也在不断更新和丰富着自己的“南方”概念。无论是近几年来黄锦树、黎紫书、贺淑芳等马来西亚华人汉语文学写作者的异军突起,抑或林棹、葛亮等“南方”书写者倍受注目的鲜明风格,都让人们重新思考和定义华语文学“南方”的边界与意义。
早在2021年,《南方文坛》杂志便发起过一场有关“南方”的专题讨论,参与的学者划定了一个“新南方文学”的地理坐标,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江南小桥流水、精致细腻的“南方”,“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新南方”。而这个基于文学创造和想象的“新南方”,带给我们的是有别于传统审美的“蓬勃的陌生”和“异样的景观”,那里杂花生树,波澜壮阔。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在为“新南方”这一文学地理概念正名时引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的观点,“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在谢有顺看来,对“新南方”的发现亦是一种文化上的展扩——它意味着潜藏在这些地方的文学元素、文学气质有机会被照亮,从一种文化中心形塑的美学秩序中挣脱出来,发现更多地方性经验。
“新南方”的横空出世或可看作是一次小小的文学“新生”,它表明“文学不是只有一个标准,不只有一个中心,文学在自由和散漫中最易生长,必须不断发现新的生长点,并让这些点在中国各地各有所成,这才是中国文学最具活力的状态”,也是我们在以下新书中想要展现的新南方写作的生长状态。
以“南方”为坐标的文字试验
“在世界性视野中,‘南方’是一个复数,也是一个移动的坐标。新南方写作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地域属地,而是以‘南方’为坐标,观看与包孕世界,试图形塑一种新的虹吸效应。它能够突破传统的地域界限,并在狭小文化囿制中脱化开来,形成敞开式的文化形态。”曾攀在《新南方写作》一书中否定了“南方”的地理意义上的局限,他引用博尔赫斯小说《南方》来说明“南方”的精神谱系属性。
在《南方》中,主人公胡安·达尔曼经历了一场精神历险。关于如何理解这部小说,博尔赫斯自己曾提到三种方式:一是真实之事,二是幻梦与寓言,三是自传性写作。对他来说,南方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精神原点,无论身在何处,总会在必要的时刻,回到那个生命的源发地。在曾攀看来,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已经构造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南方”,而“南方”对于汉语写作者也并不陌生,王安忆、苏童、格非等作家一度也为当代中国的“南方”赋形,但“南方”在新世纪,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正在实现新的汇通,它依旧作为生命的源发地和灵魂的归属地而存在,在这里,“认同与排斥、经验与想象、野气与庄重之间,蕴蓄着丰富的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黄锦树的小说《雨》中,南方芜杂密集的雨林与繁复纠葛的内心互为映照;黎紫书的《流俗地》将日常的讲述、庸常的个体、生活的万象,织进马来西亚的时代历史、社会政治之中;在《蛋镇电影院》里,朱山坡的“南方”创生出自外于己的未来性;福建作家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将“南方”作为一种想象性的装置,重新思考多维的宇宙空间和人类前进的动力;海南的林森通过《岛》,探讨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处境;东西的《篡改的命》,霍香结的《铜座全集》,林棹的《潮汐图》,传递风土和神话的交汇;葛亮的《朱雀》《北鸢》和《飞发》,融铸城市、家族、人文、历史的开阔书写;林白的《北流》诉说女性的身心历程……
同样被纳入曾攀的“新南方”书单的还有: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以知识分子的非虚构视角深入社会底层的褶皱,代表着粤港澳大湾区写作的多元探索;澳门诗人冯倾城的《倾城月,倾城诗》,以古今诗体传达当代澳门的生命经验;香港作家周洁茹的《在香港》,写尽香江之滨的喜乐哀愁、家长里短、浓汤淡饭……
曾攀以他的“新南方”书单,诠释“南方”一词在地理和精神维度的同一性,那是一种包容了多元化的内在趋同,一种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整合。正如王德威在为《新南方写作》这本书作的序言中所说:“在林白的女性心路也是身路历程里,东西的庶民命运的赌局里,朱山坡幽暗的乡土狂想曲里,林棹的灵蛙的越洋传奇里,还有其他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字实验里,我们见证界限的跨越、理性的逾越、幽灵的穿越。”
与世界主义的亲密对话
“你在梦中离开那栋房子,来到了月台,并在梦中随手找到一张邮局包裹的包装纸写下这封信给我。/你却在梦中跨越时代,错误地送到我这里来。/我与你这封信所要致予的对象也是全然叠合的同一人。显然,在现实中各种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并存。”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贺淑芳在《时间边境》中的句子。在这本囊括了11部短篇的小说集中,有的篇章极短,常有无男相无女相的幽灵,搭乘烟霾中的列车往返;原以为终结了的旅程,忽又重新开始;逃离某地想追寻一个新的自我,又发现这是永无终止的过程……你很难概括小说中具体的故事情节,甚至于评论家都在提醒作家“此时此地的现实是个重要的选项,不必清除得太干净”,但贺淑芳细腻且富于画面感的笔触,却能跨越国境和地理时差,将读者带进某种熟悉的情境,直击每个人内心那共有的,细微的,从未被照亮或承认过的痛点与感受。
同为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黄锦树在贺淑芳的书写中看到香港作家西西的影响:“西西的影响所及应不只是语言,而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是那种耽溺于幻想的倾向,以及明显的世界主义。两者是紧密关联的,后者更意味着是与世界文学近乎亲密的对话……”黄锦树所谓的贺淑芳与西西小说中呈现的“世界主义”,尤指“拉丁美洲文学以博尔赫斯为首、集大成于马尔克斯、带着强烈幻想色彩的作品,也包括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布扎蒂、艾柯等人的文学实验,直至从布鲁诺·舒尔茨到米兰·昆德拉的东欧文字实验,以及1960年代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1980年代后的中文小说变革”,在他看来,这些来自世界不同风格文学写作方式和技巧的融入、影响,也反映了马华文学新一代的阅读水准和品位的提升。以短篇《时间边境》为例,小说标题乃至章节多重时间,歧路花园,梦,镜子,甚至平行宇宙的意象,都会让人联想到拉美文学典型的奇幻叙事。黄锦树更是认为,《时间边境》明显是对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被侵占的房子》的改写,或者说肌理更丰富的(博尔赫斯式的)重写。而卡尔维诺关于“轻”的主张、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对天真而残酷的童话的回归、避免让文学陷入现实的泥沼等,也让贺淑芳远离了马华文学自身的左翼文学革命性的传统,展现出面向世界文学的意志。
提及背离马华文学传统的新一代马华文学,就不得不提及黎紫书和她近几年来倍受注目的《流俗地》。王安忆曾将马华文学的左翼文学传统概括为一种“战斗的姿态”,但这种姿态却淡化于黎紫书以较之贺淑芳更为华丽的语风讲述的一群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故事《流俗地》中了。在铭刻民族创伤之余,黎更愿意想象一种和解与救赎的可能,为小说注入温情,这似乎成就了马华文学的另一个层面的世界主义。在《流俗地》中,出现了印度文化中的象神迦尼萨的意象,印度人拉祖与象神的意象直接有关,他对女主人公银霞童年的成长产生着影响;小说里还写到教银霞打字的伊斯迈是一个马来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马来文化,共同构筑了女主角世界主义的精神世界。
波澜壮阔的海之想象
学者王德威将“新南方写作”的特征要义概括为四个关键词:潮汐、板块、走廊、风土,而这四个关键词都与自然、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并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个引人注目的地理特征——海洋。这也是曾攀在《新南方写作》中重点涉及的内容。在他看来,不论是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的深海梦游,林森“海之三部曲”的现实体会,都以海洋的神秘与疏离为底色;陈继明的《平安批》,也是写一代华人下南洋的原乡情怀;林棹的《潮汐图》,所讲述的则是一只十九世纪的巨蛙的海上周游与水底奇遇。跟随巨蛙,从珠江三角洲直至大英帝国的海上游历,让我们见识了文学无远弗届的海之奇思。
海洋的深邃与广袤,航行指向的冒险与未知,自然激发了波澜壮阔的想象与创造。生活在海南岛的林森今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唯水年轻》,收录了三部中篇《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人心与大海,各怀尺度,彼此丈量,“新南方写作”在新的时空维度呈现出人与海更为复杂的关系。小说集《唯水年轻》中三个独立中篇,各自讲述人与海在不同时空的交集:《海里岸上》是半个世纪南方海里岸上时空的交织叙述,映现传统与变迁、怀旧与坚守的主题,小说中的老苏怀一腔热血:“若登上的是被别国侵占了的岛礁,老苏还会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木牌插下,上有大红油漆文字:‘中国领土不可侵犯。’……那些年里,捕捞不仅仅是捕捞,也是凭着一股中国人的热血,在自己的海域巡游”;《唯水年轻》讲述“酷炫”的水下摄影师与海底神秘“龙宫”的百年神秘过往;《心海图》是鲁滨逊式的精神内核,昭示出走与归家的永恒主题……三部小说连缀起来,就是一部南中国百年风云史。作家韩少功评价这部小说集:“在作者那里,海洋先是猎奇和配景所需,然后渐成世俗现场、生命伤口、诗学寓言,一步步通向文学的深海。前人的农耕叙事业已数千年,作者挂帆远去,正在深耕一片蔚蓝色新的可能。”
林森让读者触摸到了海的陌生与新奇,也触摸到人心的柔软与深邃。而这片海自有其“南方”的独特景观叙事,如评论家张燕玲所言:“深邃辽阔,野气横生;人物和情感鲜活疯长,洋溢着南方蓬勃陌生的异质性。”另一位评论家杨庆祥则更为关注“新南方写作”的时代属性,在他看来,南方数代人与海洋相依为命的故事,囊括了四大主题:深情、渴望、离散、回归,三部小说的格局和气象正应和着“新南方写作”的潮汐奔涌,也彰显了“新南方写作”的海洋性特质——纵深的海洋书写,不仅是一种地理题材,背后也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土地想象的美学。而要重新发现“南方”,就是重新发现海洋,发现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气候、风俗、语言和日常伦理。
蓬勃而异样的新南方乡村叙事
荷官发牌、名品店售货、小孩子表演乐器都用白手套,而越南女佣曼达戴的是红手套,洗污糟通屎渠,作为手套之家的闯入者,她有怎样神秘的过往;每年九月初六,渔村仁海村都要举行鱼王祭,像西游里陈家庄一难一样,会有两个孩子被选为“童男童女”,这一年,完成“献祭”仪式的却是两个男孩儿;“我不是你仔,我是你走仔(潮汕方言:女儿)”,不愿意走入婚姻的走仔吴文霞回乡照顾生病的母亲,不得不直面这么多年横亘在母女之间的冰川,除了把对方越推越远,一个女儿还能做什么……10个发生在潮汕、香港、澳门等地的南方故事,描绘了诸如年轻学生、女性劳工、疯女人等角色,她们在新旧文化中、在疯狂与理性的交替里探索着自我秩序,努力活出自己——
这是作家黄守昙的小说集《走仔》里的“南方”,女性身上那种在任何境遇中都善于自省、勇敢行动的强壮的活力,以及灰色地带的幽暗传奇,活色生香的南国风致,都对应了评论家们对“新南方写作”美学风格的两大普遍认同——“蓬勃的陌生”与“异样的景观”。在黄守昙这里则具体表现为细腻的南方生活细节、成熟的小说语言、精巧不做作的叙事结构,以及对欲望、风俗的大胆表现,对当代年轻人精神困境的聚焦。他向读者呈现了90后作家的蓬勃、独特想象。
“黄守昙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南方风情:多语言的移民生态,最独特的是一脉‘我家的男人整体更像外人’的南方女性生活史。”这是作家张怡微对《走仔》的评价。据说,出生于潮汕地区的黄守昙有五个姐姐,小时候常常与姐姐们在狭小的家里共度时光,他们一起开发出各种有趣的游戏,为了打发无聊时光,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还给最小的姐姐编故事听。“那时候,我就享受虚构和虚构被人信服的乐趣”,正是这样的家庭建立了黄守昙大胆书写女性的信心。他笔下带着民间色彩的故事里,男性多为缺席,在不断地地域流转间,展现出坚韧的女性力量。而出走的男性都像是异世界悬浮的符号,在死亡或消失中为女性力量腾出广阔的舞台。
如果说黄守昙的《走仔》是新南方乡村叙事中的女性传奇,陈崇正的《香蕉林密室》则是一则有关新南方乡村叙事的寓言。
小说以碧河镇半步村陈家、关家和祖家三家人的生命遭际,串起改革开放后直至未来漫长时代变迁中几代人的精神图景,而故事本身却有点匪夷所思。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里,二叔陈大同当过阉猪匠,捕过蛇,他源于守护爱情的冲动,盘下了一片地表荒芜、地下满是洞穴的丘陵地,自己绘制图纸,打通一个个洞穴,在土地上种起香蕉林。陈大同把香蕉林密室视为爱情的宫殿,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拥有过这份爱情。香蕉林密室的功能不断翻新,洪水成灾时是避难所;后来又成了孕妇的隐身所;它还是看押疯子的监护所、逃犯的藏匿所、处置仇人的施刑场……更为重要的是,香蕉林密室充当着时代话语在现实中的微观投射。围绕这个“密室”生发出的传说,诸如外星人基地、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折叠了的多重时空等等,也让这里成了旅游地标,带动了整个村子的房产开发……《香蕉林密室》收尾于父亲陈大康的“死”。陈大康选择割下头颅,保留自己的记忆,以便未来某一天再次于“美人城”中复活……那颗头颅的命运,以及密室后续的故事,在陈崇正的另一部小说《美人城手记》中延续,这部面向未来的长篇里,陈崇正继续探索机器与人类、科技与现实、激情与异化等诸多新锐问题。
半步村、香蕉林密室、美人城,已经成为“新南方写作”领域里无法磨灭的坐标,在突破现实束缚的“南方”,陈崇正展示了腾空而起的优美姿态,那是民间传奇与科幻现实结合的新姿态。
据此,我们也将再度引用曾攀在《新南方写作》中的观点:边地充沛的野性及诡谲的景象、区域链条中文化的复杂联动、海洋文明的广博盛大、发展与开放并置的国际视野,由是引触新的融合及创造,在充满未来可能的衍生中,不断激发“南方”的新变、新义与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