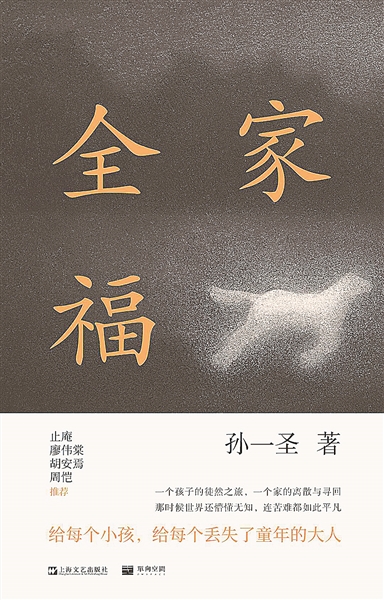
《全家福》 孙一圣 著 铸刻文化/单读/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04

■电影《光阴的故事》剧照

《云落》 张楚 著 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2024.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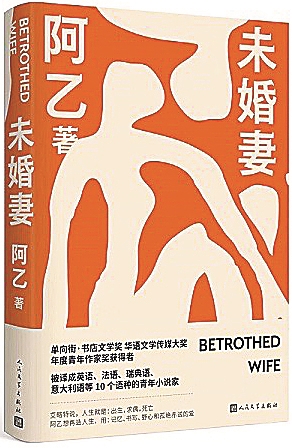
《未婚妻》 阿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中年妇女 恋爱史》 张楚 著 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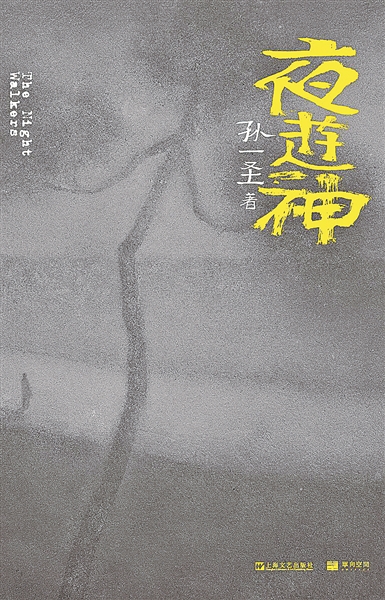
《夜游神》 孙一圣 著 单读/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歌里有云“小城故事多”,原来并非妄言。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位中国女作家写下20年代东北小镇呼兰河的故事,呈现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生活,她笔下的呼兰河真实而平凡,上演着悲欢离合,充满生机活力。与故事里的呼兰河同时代的西方,奥匈帝国治下的一位作家虚构了一座城堡,城堡所在地也是一处遥远的小镇,现实与荒诞在这里交叠,最终逼迫主人公走向绝望……
一百年后,当孙一圣以曹县的童年记忆为蓝本,书写半自传体小说《全家福》时,他同时获得上述两位作家的跨时空指引——萧红带来散文式叙事结构的灵感,卡夫卡则给予他始终追寻的描摹生活的质感。他以一个被迫从县城向着城市和家人奔跑的孩子的视角,细致呈现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
作家张楚,则直接虚构了一个名叫云落的县城,原型是家乡滦南。这座虚构的靠海的县城里有物欲、情欲、食欲,还有草木、鸟虫,充斥人间烟火、饮食男女,县城里每一个登场的人都拥有丰富的声音和性格,张楚展示他们的琐碎与不堪,也呈现他们毛茸茸的幸福。
同样钟情于县城写作的还有阿乙,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赣北的一个县级市瑞昌为背景,26岁之前那里承载着他的人生。小说《未婚妻》就讲述发生在县城的一段爱情记忆,显然,在中国的县城,爱情从来不能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全家的事……在阿乙看来,小镇文学抑或县城文学,天然具有一种更贴近现实生活的质感——揭示当地人内心的压抑、困苦、自卑、寡淡、绝望,一种被放逐的现实,“不是我们要把县城塑造成那个样子,是县城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张楚对于县城的理解更偏于理性,他说,县城是一个奇妙的存在,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融合了二者的双重特点,它是时代精微而准确的缩影。在县城里生活的人们,一方面紧跟工业文明的脚步,另一方面,也保有农耕文明的某些传统习俗,在这种和谐又矛盾的观念中,时间既是快的,也是慢的。大事件、大节点对县城的影响也是如此,不是迅雷暴雨式的,而是绵绵细雨式的。在缓慢又迅疾的时光流转中,人们明白了什么,然后又遗忘了什么。
此前,人们对于县城气息氛围的直观认知,大约都来自贾樟柯的系列电影作品,而更趋个性、深入且细腻的县城故事讲述已经在文学中展开。据说,看过张楚的《云落》后,作家孙甘露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前,中国的县城更多由电影在表现,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故事要由小说来讲了。
被县城塑造的作家
山东菏泽曹县人孙一圣到青岛推介他的新书《全家福》之时,正赶上菏泽因为草根网红郭有才冲上热搜,社会底层年轻人努力寻求出路与注目的特质,或许正契合了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孙一圣讲述了他平庸甚至有些不堪的人生开场: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家里始终很穷,种地之外,父母想多赚些钱,就到镇上卖布,卖鞋,上高中时,父亲把所有能做的小生意几乎都做了一遍,结果还是欠账,只能贷款还账,全家不再有欠账焦虑源于父亲后来去做了灵车的生意,拉去世的人去火葬场,这让家里捉襟见肘的日子稍显宽裕。
父母希望孙一圣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在城市找一份好工作,但事与愿违,高考复读四次,考了五次,虽然自称已尽了最大努力,孙一圣还是没考上一所本科院校,他上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学的化学专业,毕业后又不得不回到家乡,在镇上的水泥场做了保安。作为一个不安分的小镇青年,孙一圣抓住了一个去上海酒店做服务员的机会,在上海,他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思来想去,唯有从未中断的阅读累积给予他小说写作的底气。从上海到郑州,他投身创作,并将简历投往北京,附上当时自己所有写过的作品……就这样,从县城出发,孙一圣一路去了北京,他在那里重新发现了塑造自己的县城,并把它写进小说。
《全家福》里的主人公“我”,也从县城出发,他的目的是去寻找家人。这是留守少年赵麦生在一天里遭遇的故事——他与姐姐分别在爷爷、外公家吃饭,吃腻了就互换。他们的父母在菏泽打工,一个在夜市卖饺子,一个吃住在工地。因为一张必须上交的照片和学费问题,“我”也就是赵麦生,不得不回爷爷家、姥爷家,又不得不乘坐机动三轮车去菏泽找寻父母。一天的行程,他走过学校走过夜市,走过铁路走过土路,走过路灯走过枣树。眼前是向远方伸展的路,脑子里是记忆画面的闪回,家何以离散,与姐姐之间的“陌生”等等家庭的琐碎纷至沓来。一个小孩的视角串起一家人的生存状况,读者跟随少年体验人生的艰难。像是孙一圣在小说的题记里引用动漫《银魂》中的对白:“和你们这些少爷不同,我们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你会发现那些县城的书写者都倾向于成为不甘的“逃离者”,而他们的回望方式通常都是理性而疏离的。几年前阿乙接受采访,回溯瑞昌对自己秉性的塑造,尽管26岁后就离乡飘荡,但他称,县城几经翻修,他仍能够闭眼穿行其中。他从没有从心态上顺利地成为一个城市人,“倘若我鼓起勇气以城市为背景写作,也只能把这个城市比较浅薄、局促、窘迫、临时的一面展现出来。在所有的城市里,我都缺乏丰富的生活和社交,缺乏关系。而小说,除非太过哲理性的小说,它总是离不开生活、社交、关系。”
阿乙的生活、社交和关系永远留在他熟悉却又曾想逃离的县城。他逐渐认识到,人其实带着他所代表、依靠的地理历史生活。出身再明显不过地塑造一个人的气质。甚至我们能看出一种普遍的性格。“对像我这样出身于自尊心洼地的人而言,不会有什么天然的意气风发、潇洒自如,有好事加身容易露形,容易忘形,大多数时候,则表现得自卑、自疑、压抑、困苦,还有害怕。”或许这正是小说气质与灵感的来源。
平凡而蓬勃的典型气息
与孙一圣和阿乙对县城的青春期逃离不同,作家张楚在他的县城——河北唐山的滦南县生活了近四十年。在写小说《云落》之时,他已定居天津,仍然每个月回一次滦南。“滦南就像是一个老巢,有些陈旧和闭塞,可我的亲人和大部分朋友都生活在那里,于我而言,滦南就是我的福祉,我的疗伤之地。”
不久前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世界春天般醒来——张楚《云落》新书分享会”上,评论家黄德海表示,与大城市的独门独户不同,县城是一个大家族。小说里之所以人物众多,就是因为县城中每个人都可能彼此熟识。在黄德海看来,如此牵丝攀藤的人际网一方面成为“逃离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生活更具“人情味”。黄德海举他最喜爱的人物万樱为例。在他看来,万樱类似于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看似混沌却活力四射,即使遇到困难也照旧能够活得生机勃勃,“为了生活,她顾不得伦理道德的束缚,自然地展现出她的欲望与需求,如同古语所说,‘礼不下庶人’。”在作家程永新看来,《云落》主线虽围绕万樱展开,但由于人物众多,张楚从众人的视角叙述故事,从而让人物贴近生活本真的样态,“比如万樱身边的男性性格各异,与万樱组合而成互不相同的磁场,这些磁场也构成了县城的网络,而这一网络就是微观的中国现实。他由此表示,小说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个典型县城的样本,云落县城如同一个微观社会,读者能够从中窥见中国的细微生态,比如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它也浓缩了中国所有的风土人情,包括它的丰盈与缺憾。”
相应地,《云落》里的世界尽管不完美,但也并不悲惨。这也是黄德海觉得这部小说吸引他阅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之所以喜欢这个世界,是因为它充满活力。小说描述的生活,就如同现实生活本身那般有滋有味,不同性格的人物都能够舒畅地活在其中。”黄德海形容这部小说写的是“参差人间的春醒时刻”,就像春天刚醒来,让人联想到春日复苏,昆虫活动,绿意渐浓,“正如里尔克的一句诗,‘如果春天要来,大地会使它一点一点地完成’。”
而张楚坦言,他之所以能将小说写得满含情意,与他创作时的心态有关。他写这部小说时,人在天津,“当你从一座城市回望另外一座城市时,内心有一种仪式感,好像要穿过无数树木、村庄、铁轨、河流、工厂烟囱,才能抵达你的故乡。”正因怀抱朴素而纯净的爱,小说中并没有彻底的坏人,而是一群最普通的人,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于是,读者也跟随作家回到了县城里的裁缝店、窗帘店、理发店、小饭馆,听见街巷里各种嘈杂又重复的声响。
或许,张楚并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在写作中去思考社会和时代问题,只是如他所说,随着人物路径自然行进。他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名为《中年妇女恋爱史》,其中那些绽放着光芒的女性特质,也进入到虚构的县城云落,成为人们理解今日中国县城的独特切口。而这些普通人物的普通日子,却又正是大时代褶皱里最真实的人生风景。
写出真实生活的质感
“没有兴亡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变迁,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只有在一个长镜头下被我们遗落的人间真实。”这是孙一圣对小说《全家福》的自我概述,对于张楚的《云落》似乎同样适用。
何为人间真实?在《云落》里,可以是不起眼的食欲。“吃”在这部小说里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存在,小说里写到各种食物,有滋有味,并在细密绵长的书写中呈现了“吃”于普通人的意义: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口味偏好,似乎都构成他们的生命底色,每一场席面、宴会也见证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这也是张楚的刻意所为,他说,日常生活通常都很琐碎、干瘪、油腻、无趣,缺乏幻想中的诗意,可如果我们赋予日常生活一种仪式感,它肯定就会变得不一样,比如饮食,对应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舌头和胃,也对应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传统的审美。小说里写到三到四次大规模的聚餐,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融合人物关系,另外一方面则见证着人世间最庸常的悲欢。
而对于《全家福》而言,遗落的人间真实存在于诸多细节的处理中,孙一圣将之理解为真实生活的质感。在他看来,写小说要建立一种场景,给读者以画面感。他提及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天路历程》,开头这样写道:“我在旷野里行走,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个洞穴,我就在那儿躺下睡觉,我睡熟了,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那儿,背后就是他自己的房子,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背着一件看来很重的东西,我看到他打开那本书,念着,一面念一面不住地流泪,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发出了一声悲伤的呼喊:我该怎么办呢……”这一具有画面感和节奏感的行动描述,带出了“我该怎么办”的普世性发问,而它所具有的语感和氛围会更加让人记忆深刻。
再进一步,如何才能建立此种语感和氛围?孙一圣提到卡夫卡的小说《公路上的孩子们》,其中描写一辆马车经过一个花园的瞬间,卡夫卡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观察方式:马车经过花园时,花畦暗了一下。孙一圣没有错过这个易被忽略的细节,他认为这种文学性的描述正是小说所体现的真实生活的质感,它彰显于故事的进程中,而并非结局的戏剧性。而他一直在努力想要写出同样的句子,表现出细致入微的生活质感。
在《全家福》的序言里,孙一圣再次提到卡夫卡的《公路上的孩子们》,其中写一群农村的孩子于傍晚玩耍,细节丰富且玄妙。在这篇小说里卡夫卡写出了一种他独创的“运动性”,犹如电影的运镜。“小说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没有目的,没有指向性的意义,同时又意蕴丰富。只对场景做类似镜头般的描摹和观察,没有画外音,有的只是自然的白噪音。里面只有小孩子的跑动,没有说明,只有关于跑动的描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也没有离开的原因和动力,甚至连前进的方向(尽管说了去哪里,却没有说去做什么)也意义不明。没有目的的行动最为致命。来到结尾,孩子们一个个都被父母叫回去了,主人公‘我’却想要离开家乡到城市去……”
《全家福》也是写一个居住在县城的孩子出于某种意外,孤身向城市进发的故事。作家写道:“如果说《公路上的孩子们》是孩子对前路的未知向往,那这部《全家福》则是孩子对这种未知向往的开拔。”孙一圣说,他试图用小说写一部电影。
孙一圣也希望他的小说同时具有散文的质感,为此他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写,从农村到城市,穿过平原上的麦田,还有行车道路两边的树木,房屋,小说里有一个比喻:在坐上机动三轮车看到自己的家时,小孩感觉一脚就能把他的家踏平。他直言这有一点借鉴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段段地对小时候的回忆,像是一篇散文,还有一点致敬沈从文的《边城》,“他写得十分纯真,这也是我想要追求的——纯真感,呈现一个孩子的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