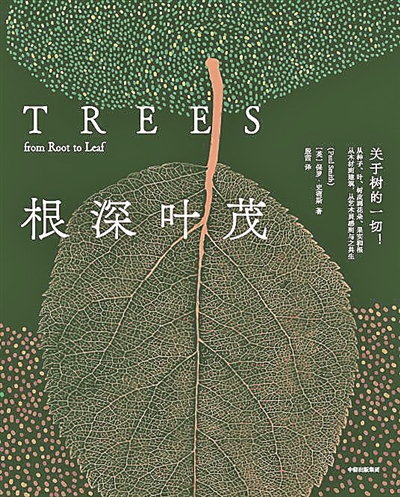
《根深叶茂:关于树的一切》 (英)保罗·史密斯 著 殷 茜 译 中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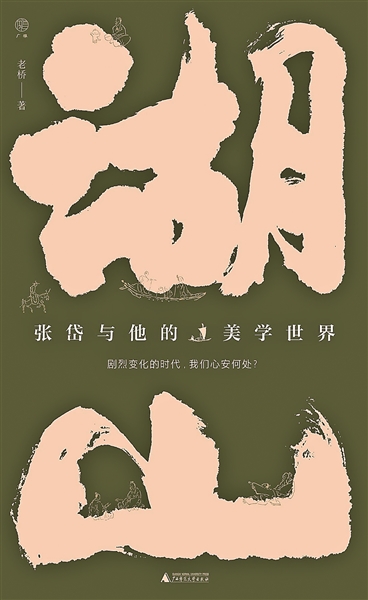
《湖山》 老 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园林漫步》 刘天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苦闷的象征》 (日)厨川白村 著 鲁 迅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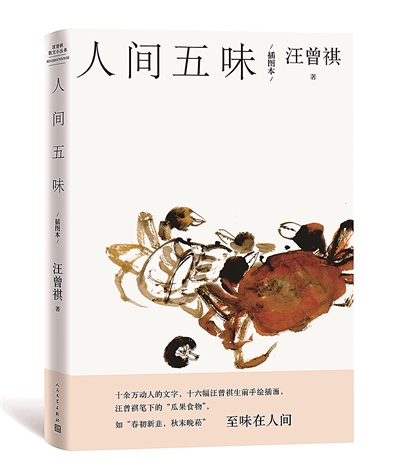
《人间五味》 汪曾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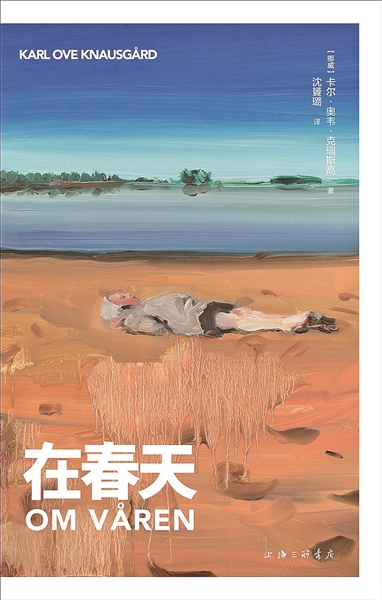
《在春天》 (挪威)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90年前,丰子恺写“春天”,他说,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季节,尤其是暮春以前的春天是很不令人愉快的,“一日之内,乍暖还寒,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淇淋,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料峭’的滋味。”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明确的,而或许正是这个季节的忽冷忽热、阴晴不定,才足以激活人类日益麻木的感官,回归到碳基生命富有自然灵性的本初。
上周青岛早春的榆叶梅与杭州法喜寺500岁的玉兰花一齐盛放,提示我们自然万物的感知足以穿越时空,彼此共情。春的色彩同样会穿越文字的时空:从波斯诗人与美酒、灵魂相伴的哲思花园,到中国北宋年间欧阳修“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琅琊山之游、司马光“兴会神到”的园中独乐;从隐藏在19世纪美国总统杰斐逊三月日记里的五畦芦笋与一畦豌豆,到穿越数亿年、拥有6万种类、赋予人类灵性却被长期忽略的树;从“生活家”汪曾祺笔下总会在春天想起的寻常中透着不寻常的人间至味,到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如实记录下的生命美好与爱的觉知……
有人说春天并不是适宜读书的季节,因为万物生发、感官的灵敏度陡升之时,一切都要从触摸与试探开始,就像久石让在他作曲的《龙猫》歌词里写的那样:“去散步吧,去森林里散步,去草原上散步,去小溪边散步,说不定就会遇到森林精灵。”久石让相信,在勇于尝试新体验的路上,在与世界的碰撞之中,不期而遇的幸运就会降临。而恰是在阅读中,在文艺的熏陶下,我们才获得了有关春天的行动法则,明确了春天要做的事。英国作家约翰·威廉·斯特林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春天说,勇敢的人要先享受春光。
唤醒感官——
从纪念一位“生活家”开始
2024年惊蛰这一天,也是著名作家汪曾祺的104周年诞辰纪念日,他一生走遍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无论水草丰茂,还是风沙遍地,都留下活色生香的独特印记。这位出生在春日萌动季节的文学家,天然拥有将寻常食物吃出人间情味的敏锐觉知。
他眷恋故乡高邮,会用对食物的描摹来表达:“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作‘硃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那简洁而形象的“吱”的一声,足以激活所有食欲,击退所有春困。他描写春令时鲜鳜鱼入菜:“鳜鱼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清蒸、干烧、糖醋、做松鼠鱼,皆妙。汆汤,汤白如牛乳,浓而不腻,远胜鸡汤鸭汤。我在淮安曾多次吃过‘干炸花鱼’。二尺多长的活治整鳜鱼入大锅滚油干炸,蘸椒盐,吃了令人咋舌。至今思之,只能如张岱所说:‘酒醉饭饱,惭愧惭愧!’”
食物也是他追寻故人记忆的方式,他回顾西南联大的“七载云烟”,对“滇菜”念念不忘,无论是学生党借以开荤解馋的汽锅鸡、还是名门才女张充和亲制的“十香菜”,都饱含青葱岁月的甘美,在对“五味”的描绘中不着痕迹地寄情怀人。
说到爱逛菜市场:“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儿,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草,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的乐趣。”汪先生的文字总是弥漫热腾腾的生活和恬淡的趣味,也有人说像潮州的一些汤,看上去很清,白开水一样,喝起来却极为鲜美,因为是用文火慢慢炖煮出来的。
盘中五味,亦是人生的百般滋味。汪曾祺是文学家,更是“生活家”,他寄情于食物、风物、器物,把曾经的经历,甚至是那些残酷的故事深隐于看似平淡的烟火气息之中,对它们保持孩子一样充满新奇的热情,让我们以春日的感官重新打量生存的世界。这或许正是我们纪念他的意义。
游园寻乐——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汤显祖《牡丹亭》中这句脍炙人口的唱词可不是随便说说,它告诉我们,春天“逛公园”的传统由来已久,明代园林与寻常百姓的生活已相当密切,游园赏景已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文化活动。
何为园林?浓树、芳草、清泉、美石,这些充满山野自然气息的美物几乎是中外园林的标配,与自然另一种形态的交融,无疑是步入文明社会的人类共同的真挚回望。尽管遍布世界的园林风格迥异,但人们不约而同都将游园视作一件赏心乐事。17世纪英国哲人培根说:“全能的上帝率先培植了一个花园。的确,它是人类一切乐事中最纯洁的,它能怡悦人的精神……”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对人生真谛的诠释也少不了一个“乐”字,而寻乐的一个主要场所就是园林。古典园林研究者刘天华在古人那里找到游园寻乐的确证:这个春天刚面世的小书《园林漫步》中,他提及欧阳修“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琅琊山之游,钟情园林的司马光“兴会神到”的园中独乐,晚清颐和园中的乐寿堂、谐趣园,江南海宁安澜园以“三乐”命名的厅堂——“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及时行乐”。
游园所寻之乐何来?根据美学家的研究,一般的味觉刺激仅能引起快感,但如果与视觉、听觉协同而产生通感,味觉就会上升为审美感受。书中举一例:“就好比人们在家中喝瓶装的矿泉水,基本上得到的是味觉的快感享受。但如果人们来到青岛崂山,在道观中静坐品泉,耳边是松涛阵阵,眼前是海天一色、岛屿沉浮,身在古树的浓荫下,习习凉风扑面而来,那么此时甘甜爽口的美泉之味无疑将上升为这一邑郊园林胜景中不可分割的审美感受。”环境如画的园林欣赏空间,使泉水的味美程度发生飞跃,山水园林和甘泉美水的结合也因此常常成为园林的特色景观。耽乐山水,徜徉园林,亲近有文化意味的自然,则成为人所钟情的赏心乐事。
几年前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花园的欢沁:经典文学选集》,可以看作是古今中外文人雅士对赏心乐事——游园活动的歌咏集成,从创世之初的伊甸园,到达尔文倾心的邱园,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到陶渊明归隐的菊园……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无不赞美游园之乐。
对花园情有独钟的波斯诗人哈菲兹,吟诗作赋时手里总是握着一只精致的玻璃杯,盛满设拉子葡萄酿成的好酒,死后灵柩也安放在一座精美花园中,这一场景诗人早已在《花园》中预见:“五月的草地编织着春天的童话/严肃的人也会忘记未来,活在当下/……人生是一本黑色的书/请别过分苛责/哈菲兹的棺椁经过时,请不妨追随/他虽困于罪孽,但正走向花园。”
1801年至1809年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游园中的劳作,他的园艺记录里有三月的五畦芦笋、一畦豌豆和两排莴苣,还有开花的紫风信子和水仙。在给著名植物学家、也是众多花园的设计建造者威廉·汉密尔顿的信中,他说,“没有任何文化可以和园林相比,生机种类繁多,即使不为家人果腹,内心的渴望依然驱使着我投身花园。”
在书的末尾,探讨了园林对灵魂的慰藉——《心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在花园里学会了耐心,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花园里领悟知足的哲学,英国诗人斯温伯恩在花园哀痛凋零的玫瑰和逝去的爱情,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在花园里找到未来的希望,而编著者本人也以花园为图书馆,其乐无穷。
认识一棵树——
在习以为常中发现陌生
在习以为常中,我们往往会忽略很多东西。比如此刻窗边的一棵树。正如梭罗所说:“大部分自然现象……是我们毕生无法见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自然之美,只是我们愿意欣赏的那一部分……人们只能看到自己关心的事物。”
地球上有多少种树?在2017年之前,地球上能正确回答出这个问题的人数是——0。如今全球科学家耗费数年心血通力合作,才给出了一个相对模糊的答案:约略6万种左右,但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变动,因为每年都在不断发现新的树种。某种程度上,树才是地球陆地的主人,它们见证过数亿年的漫长岁月,比起它们,人类从开始直立行走到成为万物主宰的这段历史,不过是眨眼一瞬。
树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树木,是它赋予了我们灵性。早在恐龙灭绝之初,树木就为我们的树居祖先提供栖息之地,等到我们开始直立行走,它又成为我们手中的工具、带来火种。在中信出版社三月出版的新书《根深叶茂》中,树木是神圣的、值得感恩的。无论哪片大陆,哪个民族,几乎所有文化都认为人类起源与树木相关。在北欧神话中,神树“尤克特拉希尔”是宇宙的象征,中国神话中,建木则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
《根深叶茂》的作者,保罗·史密斯统领全球植物保护领域两大机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世界上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植物多样性保护组织,2021年它首次发布了《世界树木状况报告》;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国际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建立了“千年种子库”,储藏了4万多种植物的种子。正是这位世界顶级植物学家建议我们,去从头到脚认识一棵树,不仅是它本身,还有它所承载的自然演化和人类文明的烙印,由此带来的不可估量的价值。春天,激发我们去审视那片习以为常的绿意。
抒发闲情——
借鉴一种散漫而优雅的美学生活
剧烈变化的时代,我们心安何处?如果要借鉴一种闲情野趣的古人生活,明清之际的文史家张岱似乎最为契合当下人们的心境。可能因为同样酷爱美食,他也是最受汪曾祺先生推崇的同道。二人都认同酒醉饭饱之后的几多“惭愧”,从著述到身行,知行合一地履行一种有趣而无用的美学存在,那并非所谓的躺平,而是当代人憧憬中的纵情山水、清朗舒阔、散漫而优雅的生活。
这正是作家董联桥在《湖山》中所讲述的,书中写张岱的游历,那是比今人辛苦许多的旅行。他的旅行路线沿着大运河两岸的都市,诸如今日浙江的宁波、台州、杭州、嘉兴、湖州,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淮安,以及上海松江、安徽芜湖,最远就是山东的兖州和泰安。除了老家绍兴,他停留时间最长的是杭州,因为湖畔的寄园曾是祖父张汝霖的家。“游历是张岱浪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但绝不走马观花,那个时代更不存在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张岱的旅游更像是画家写生,虽然并非用笔墨描绘山水,而是将山水的形与魂印在脑子里。或舟船,或客店,或车马,或行走,张岱游历其间,犹如过电影般,将看到的景、人、事再放一遍,用其生花笔意,删繁就简,寥寥数百字,一篇小品放入诗囊。”张岱的旅游风格,不是去研究某一地域,而是寻找当地美好的人和事、开心的玩和乐、特别的俗和雅。他所记录的往往是别人忽略的角度和内容。
在作家董联桥看来,张岱之所以成为一代传奇,诗文存世流传,至少有三个条件:一是风雅、富足、浪漫的生活背景;二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满足自己爱好的条件;三是广泛的交际、清玩的悟性和文学的天赋。他是把复杂难解的人生问题藏于看似散漫实则从容优雅的日常体验中,化作笔端冲淡平和的点染。
省察生命——
人生总要在某个季节发出残酷追问
屡屡退休未果的宫崎骏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刚刚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作品的中译名令人想起三年前出版的一本德国作者海克·法勒的畅销绘本《你想过怎样的一生》,绘画风格虽与前者迥异,却以其明亮的色彩让人印象深刻。毫无疑问,春天是适合发出此种终极追问的最适宜的时节。
记得在那本书中,逐一列出了不同人生阶段人们对于世界相似的理解,比如:19岁时,会经常讨厌自己;36岁时,发现现实与想象相去甚远;43岁时,学会了为自己而活;51 岁时,接受了父母的样子;75岁时,学会了遗忘;80岁时,感到生命有限,更加珍惜当下;92岁时,接受了人终会死亡的事实……春天似乎是更适宜开启这样有点丧、有点残酷的哲思的。
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在春天》里记录下2016年他和孩子们参与的一次颂春仪式。这是小女儿的第一个春天,这个家庭也刚刚渡过母亲生产抑郁的阴霾。与此前面世的《在秋天》《在冬天》不同,克瑙斯高不再讲述世间万物,而是以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反思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为刚出生的女儿讲述人与世界的羁绊为何物。
“天空很快暗了下来,第一批星星出现在东方的夜空里。太阳则在西边落下,地平线笼罩着一层红色的面纱。篝火燃得正旺,噼啪作响,将火焰、浓烟和旋转的灰烬抛向蓝黑色的天空。孩子们气喘吁吁,兴奋地跑来跑去,又喊又叫又笑。因为春天来了,空气中充满了轻盈、光明和陌生的感觉。”作家感叹:原来美好的事物从来没有远离我们,他开始省察自己的苦闷人生:“活着有时是苦涩的,但总有值得活下去的东西。我今年四十六岁,我的洞察力告诉我,生活就是由所有必须去应付的事情构成的。而所有与幸福相关的,却恰恰相反。”应付的反义词是什么?克瑙斯高自问自答:应该不是退让,也不是后退到你那光明与黑暗、寒冷与温暖、柔软与坚硬的世界里。也不是那些无分别的光芒,不是睡眠或休息。应付的反面是创造,建造、添加之前不存在的东西。”黑暗当然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光明中的针尖。生活当然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只是我们在中性或美好中穿行时的一条看不见的通道,迟早会从中走出来。
突然想起一百年前风靡中国的一本书《苦闷的象征》,作者是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译者是鲁迅,原本一部文艺理论书,结果却替当时的青年喊出了心中的苦闷,正如书中所言:“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对于苦闷者而言,文艺作品也是唤醒敏感情绪的必备良药,是人醒着或者活着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春天恰是最适宜读书的季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