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登上长城的段义孚。

《恐惧景观》 (美)段义孚 著 徐文宁 译 译林出版社 202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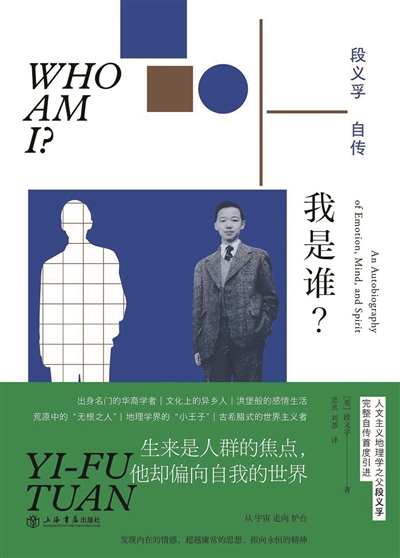
《我是谁?段义孚自传》 (美)段义孚 著 志丞/刘苏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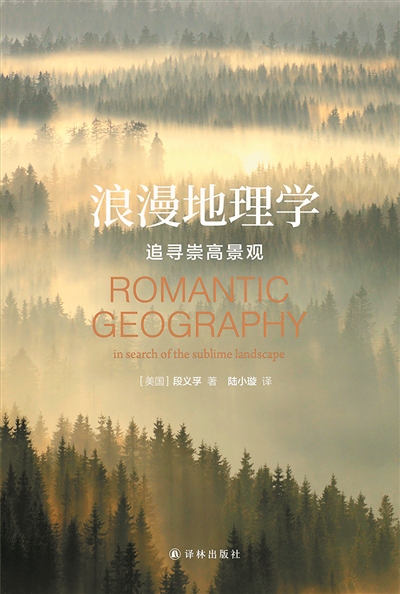
《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美)段义孚 著 陆小璇 译 译林出版社2021

《人文主义地理学》 (美)段义孚 著 宋秀葵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回家记》 (美)段义孚 著 志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恋地情结》 (美)段义孚 著 志丞/刘苏 译 商务印书馆2018

《逃避主义》 (美)段义孚 著 周尚意/张春梅 译 商务印书馆2023.10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在知乎上读到网友的图书推介:“爱地理就去读段义孚吧,你会看到一名有血有肉的地理学家,是如何从地理学的角度向人们阐释生活的意义。”地理学如何能阐释生活的意义?
2023年,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人段义孚去世一年后,他的中文版自传《我是谁?段义孚自传》和代表作《恐惧景观》相继面世,《逃避主义》再版,包括此前出版的《浪漫地理学》《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等在内的十余种个人著述,都在从不同角度回应着地理学与人类生命意义之间的关联这一命题。
一位地理学家的日益“走红”绝非偶然。据说,段义孚最为出圈的著作《恋地情结》刚出版时,一个大学书店将其归入“天文学和神秘学”的类别,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创之初也曾遭遇此番误读,在国际地理学界,段义孚被视作“异类”甚至“反叛者”,原因在于,他所谓的地理学并不局限于经纬坐标、地形地貌、气候、人口、GDP等理性的科学数据,而是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融入地理之中,转而追问地方、空间、景观、环境与人的情感、价值观的联系。作为我们心中地理世界的发现者、揭示者、解释者,这位跨学科大师以地理学为入口,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想,并借此发现人跟地方真正的关联。他赋予了地理科学不那么严谨却更加丰富生动的人情味。
段义孚曾这样阐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它能使我们有效地思考某些问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人的成长,并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作为个体,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十分短暂。问题就是:‘人,何以为人——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地理学归根结底是关于存在于世界中的个体的“人”的问题,人的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某种程度讲,是地理学决定了我们是谁,而人性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段义孚的文字不仅凝结为知识,更成为一种广为传播的人生智慧。
那些令我们感到恐惧的“景观”
人是我们安全感的最大来源,同时也是我们恐惧感的最大来源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曾经有哪些景象让你感到恐惧?对于地理学家段义孚而言,这是一个有关人的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基础性问题。
“小时候,我们会怕黑,怕被父母抛弃;当我们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或是陌生的社交场所时,会感到焦虑;我们害怕看见死尸,害怕黑暗中那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妖魔鬼怪;我们对疾病、战争、天灾深感恐惧;看到医院与监狱,内心会战栗不安;独自走在空无人迹的街道和社区时,担心会被打劫;担心整个世界的秩序会突然崩乱溃散……”从儿童期、青春期到成年期,从原始的自然之境到复杂的工业技术社会,恐惧的内容因不同生命周期和环境的发展变迁而改变,却无所不在。段义孚在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山之作《恐惧景观》中,审视人类的恐惧——
它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有两种类型的紧张清晰可辨:一种是警觉,一种是焦虑。当人远离熟悉的环境,可信赖的人群,就会产生恐惧。他引用17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一直使用的“景观”的含义——既是一种心智的构建物,也是一种自然的、可测量的实体。而“恐惧景观”的定义:既指无形的心理状态,也指有形的环境,是无法控制的、对人心理造成压力的,混乱的、自然的或人为的力量存在。
人们之所以产生恐惧,正是源于他们对世界不同的地方,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缺乏真实的了解。比如,对人死后世界的无知,对大自然威力的无力,对同类之恶的失控……于是才有了小孩子的童话,成年人的传奇、宇宙神话,以及哲学体系,这些都是人类的心智构造的庇护所,人们可以在里面栖息,暂时避开经验和怀疑的围困——这也是他的另一本书《逃避主义》的一个要义。
对于总是自言“缺乏安全感”的现代人而言,这位从严肃学术维度介入普遍现实问题的地理学家,显然激起了共鸣,但这并不是段义孚书写《恐惧景观》的目的。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周尚意在为《恐惧景观》所写的中文版导言中说,“他还要让读者体会到,在人类社会中,恐惧与克服恐惧、逃离恐惧与制造恐惧是对立统一的。我们在时刻警惕他者(人和自然)威胁时,也要警惕自己成为他者的恐惧景观;人们在营造美好家园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恐怖电影和游乐园的鬼屋。”
正如段义孚在这本书中所言:“人是我们安全感的最大来源,同时也是我们恐惧感的最大来源。他们是鬼怪、巫婆、凶手、窃贼、强盗、陌生人和不怀好意者,他们萦绕在我们的景观之中,将乡村、街道、滋养人类的校园都变成让人恐惧的地方。”
或许正是基于此,对于“恐惧景观”的系统性探究才可能给人们抱有永恒兴趣的问题提供一个解惑的新途径,比如“作为人意味着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
在地理中发现“人”的存在
即便是普通人常见的生活经历,也应该有普遍的旨趣和意义
2020年,段义孚曾在一次有关新冠疫情对人类影响的对谈活动中提到,疫情会让人开始选择更多的非人际沟通,但也让人从未如此意识到“旧常态”的可贵——那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拥抱和深度连接。他对于人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经验感知的关注度,显然超出了传统的地理学研究者。
实际上,重新感受人所处的空间与日常生活,以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维度来构建人与环境的关联,正是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想要深入探究的。他主张地理学家的关怀要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个体面对具体环境时的感知,在地理中发现“人”的存在。唯有如此,才能够恢复掩盖在逻辑实证主义与量化空间分析背后的那个同时收纳身体与灵魂的世界。“我们如何感知、构建和评价那个自然与人力共同塑造的物质环境”,是段先生一生的追问。
周尚意教授建议读者从《我是谁?段义孚自传》开始,去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要义。他建议将这本自传视为地理学术专著,从中可以理解段先生的地理思维逻辑。“本书隐含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基调,即返回到思考的存在者。个人的存在有三个方面:1. 个人对周围环境世界的体验,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经验。2.个人对其他人的体验,每个人都是以主观的方式来体验别人的。3. 自我的世界。”
把这本书与《回家记》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对照阅读,对于这位与众不同的地理学家所提出的人的“地方感”的学术概念,也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自传中,作者从未停止自我审视,他称自己是一个寻不到根的人。“年轻时从未在一个地方住满过五年,直到38岁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在那之前,我一直在不停地换住处,先是小时候与家人一起,长大后便独自一人。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位于印第安纳州)、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和麦迪逊各住了十四年,这两个地方是我仅有的可以寻找归属感的地方。在社交方面,我也同样无枝可依,原因很简单——我一直单身。一个家庭算是一片可以移动的旧土,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但我与它无缘……”这或许也解释了他在《回家记》中所言,“在我关心的个体对环境的依恋之外,始终也有一份对环境之变幻莫测的恐惧相伴随。”
地理学家回答“我是谁”,是在时空坐标中定义的,尤其是在空间坐标中。段义孚将自己定义为世界主义者,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及未曾去过的地方都有情感和判断,这种情感和判断构成了他的地方感。
作为段义孚著述最早的中译本译者之一,周尚意在去年段先生去世时再度论及了“地方感”概念的价值,面对“地方感”是老生常谈的媒体言论,他极其不平,在他看来,段先生研究地方感,是受到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影响,与“身体主体性”相关。他举例说,有时人们无需看着脚下的路面,就可以一边用手机打电话,一边走路,这时身体主体控制着脚步前行。之所以可以这样做而不绊倒,是因为身体与日常生活环境长期互动,已经形成的“地方感”。
段先生希望人们意识到,并非只有所谓独特的人、伟大的人才能洞察世界、认识地理,每个寻常的人也都是独特的人,可以通过不断地观察世界、感悟世界,生成自己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观念,从而更清晰、更自主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正如他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写的:“即便是普通人常见的生活经历,也应该有普遍的旨趣和意义。”
关于地理学意义上的理想人生
一个美好的地方,其建筑物不仅能愉悦人的感官,还能温暖人际关系并增进人的福祉
回到人文主义地理学能使我们有效思考的那些形而上的问题——“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是谁?》中,段义孚在对“美好的人生意味着什么”的探讨中,代入了地理学——
“人们会如何描绘一个美好的地方呢?对我来讲,一个美好的地方必定有好的天气,好的自然环境而且物产丰富;其建筑物不仅能愉悦人的感官,还能温暖人际关系并增进个人的福祉。这些都是一般性的要素。如果谈到一些特别的要素呢?那就肯定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了……在现代,地方已呈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包括各种类型的农场、村庄、郊区、城镇和都市。截然不同的特性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对于农场来讲是好的要素,对都市而言不一定是好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好’一向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什么好?以及什么才算好?都是会出现的问题。……对人类而言,美好是同人的潜质和认识程度关联在一起的。”
而在《恋地情结》中,他这样解读“理想的环境”:“它从根本上可能会是两种相反的图景:一种是纯净的花园,另一种是宇宙。大地的产育给我们提供生活的保障,而星空的和谐更增添了几分宏伟。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凉到天空之下的疗伤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他认为,不同文化中的人类孜孜以求的环境通常包括两种基本的意象,一是象征安全感的“花园”“家庭”“郊区”等;另一类是象征自由的“宇宙”“广场”等,这两种意象构成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而为了调和,人类也在不断努力地寻求中间的第三元。
研究段义孚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叶超认为,段先生是在通过地理学这个途径,解决他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他从自己出发,从个体的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最核心的思想,并用一系列的论著来解答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恰恰切中了现代人的要害,形成了扩散效应。
后全球化时代的地理学
人不断对世界、对自己发出新的问题,这样的能力是目前技术不能够完成的
“似乎每个人都在问。不仅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都会问自己‘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段义孚在他的自传前言中说,“自我意识减弱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和地域的流动性增强以及科技的快速革新,正如专家们所说,我们正处于身份危机之中。”而他早已预见了这一点。
上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前辈李旭旦就已经将段义孚的文章引译到了国内,但他坦陈,当时并未读懂。2000年后,段义孚的论著陆续被翻译面世,但数量并不多,直至近五年,才有大量的译作出炉。专业研究者叶超透露,从翻译的角度讲,目前段先生的著作中译本在地理学家中位居第二,第一位是地理学家大卫·哈维。
那么,人文主义地理学在现代地理学思想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段义孚所致力研究的人与地方的关系,在后全球化时代又具有什么新的意义?
叶超认为,段先生的研究有一种超前的预见性。当中国的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还没到一定阶段时,他所研究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引起国内的共鸣。但是,比如随着社区中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制造宠物》就进入了视野。他其他的书也有类似情况:对于现代人所处的孤独情境以及重重压力,因为个体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他提供的样本就更加具有价值了。“他留给我们很多思想的遗产,最重要的就是朝向人文主义的世界。”
周尚意则认为,段义孚的著述打破了普遍的偏见——地理学不是高深的学问。他在为《我是谁?段义孚自传》所做的推荐语中说,“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像徐霞客、亚历山大·洪堡那样既能读万卷书,也能行万里路的人,自然比其他人的地理知识丰富。但在遥感、互联网等技术的支撑下,普通人可以迅速获得世界某个角落的地理信息,甚至用 AI生成地图和文字。因此人们认为,不必将地理作为一门需要到大学里攻读的学科。早在20世纪70年代,段先生等人提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已经回答了此问题,即人不断对世界、对自己发出新的问题,这样的能力是目前技术不能够完成的。大数据驱动让人工智能在人机对话的自然度、趣味性上有了巨大突破,但距离机器人形成完全自主意识还很远。人们基于空间(space)、尺度(scale)和地方(place)这些地理核心概念而形成的循环感悟能力、不断问答的能力,是需要在大学地理专业训练中不断培养的。”
时至今日,人文主义地理学依然不能成为地理学领域的主流,但它依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对城市规划、建筑学、文学、艺术等学科或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段义孚提示我们,理解自我与他者、人类与地方的密切关系。而这也是强化自我意识,破除身份危机的一条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