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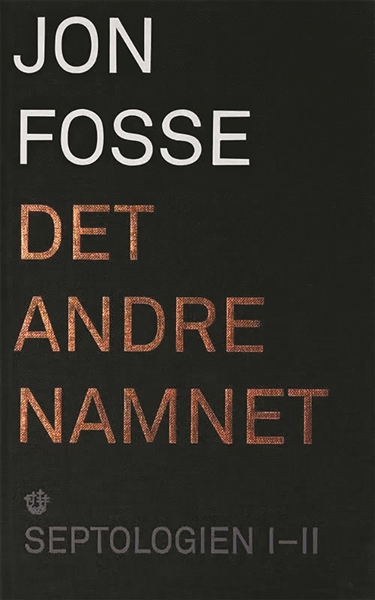

■约恩·福瑟的《别的名字:七部曲I-II》《晨与夜》的外版封面,上述图书的中文版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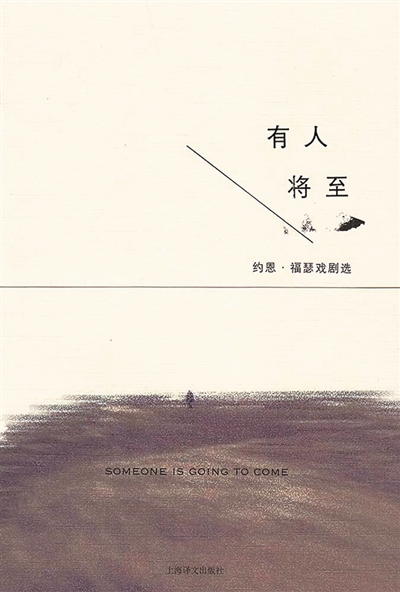
《有人将至》 (挪威)约恩·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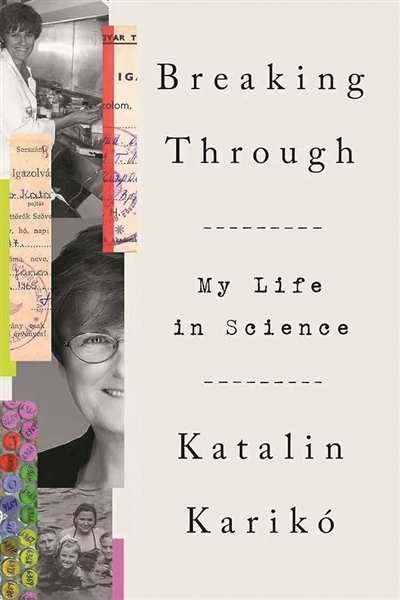
①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新晋得主卡塔林·考里科的传记《突破:我的科学人生》英文版封面 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卡塔林·考里科 和德鲁·韦斯曼,以表彰他们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使得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 mRNA 疫苗得以开发。她的传记《突破:我的科学人生》一书的英文版将于2023年10月10日出版,讲述卡塔林·考里科这位从乡村走来、苦坐冷板凳四十年的“科学苦行僧”,以一己之力改变医学未来的历程。该书的中文版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②《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 99读书人(2023版) 经《巴黎评论》独家授权,99读书人将三十四篇诺奖作家访谈归总一处,并补充作家生平及获奖信息,分上下两册翻译出版。作为一份能够定义当代文学世界写作生命精髓的记录,访谈本身即是对当代文学发展脉络的一次跟进和梳理,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当代作家迥异的秉性和不同时代的思考风尚。当读到约百年前作家福克纳说,“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就是画报和连环漫画也许有一天会弄得人的阅读能力都退化了。说实在的,文学已经快要倒退成尼安德特人洞穴里的画图记事了。”甚是唏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2023年的10月5日,64岁的约恩·福瑟驾车行驶在挪威乡间小路上,接到了一个对他而言并不算意外的电话——电话来自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因他富有创意的戏剧和散文表达了不可言说之物”,福瑟成为挪威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距离这个几乎称得上世界尽头的北欧国度的上一位获奖者西格丽德·温塞特已经过去了95年。
对于获奖,这位北欧重要作家、当代欧美剧坛负有盛名的剧作家回应称:“我很惊讶,但同时也不惊讶。在过去的10年里,我已经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谨慎的准备。”他的谨慎源于10年前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所言的诺奖“负担”:在他看来,只有到了足够大的年纪,确定获奖不会影响写作时,才算真正做好了准备。
有所准备的不止福瑟本人,早已纳入候选名单并始终高居赔率榜前端的他,此前也出现在诸多业界人士的预测名单中,包括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和99读书人出版编辑骆玉龙的预测,众人的不约而同除了职业敏感,还有一个显性依据,就是英国独立出版社Fitzcarraldo Editions的新书书单,过去几年,这份小众书单与诺奖的评选结果高度相关——这家出版社也正是上届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英国出版商,而约恩·福瑟是最近频繁出现在书单上的作家之一。
与因激烈挖掘自我而倍受争议的2022年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以及2021年得主、过于生僻的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相比,约恩·福瑟折桂无疑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内。虽然目前他作品的中译本仅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有人将至》和《秋之梦》两本绝版戏剧选,在豆瓣标记读过的人数不超过500人,但在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世界,“小众”无疑是一种常态,毕竟,即便是真书迷也未必在今年6月看过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的福瑟戏剧《一个夏日》,那又属于另一个小众的群体了。
无论如何,一年一度的诺奖评选都在制造一场文学的喧嚣,破除小众的拘囿,激发大众阅读的好奇心。只不过这一次,评委会选择了惯于置身峡湾、海浪之间的挪威西部“村民”、自称爱读书拉琴的“嬉皮士”约恩·福瑟。他笔下的世界,鲜有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主人公于遗世独立中,却始终无法远离内心的骚动……或许只有在此种远离尘嚣、内寻自我的“清冷”叙事里,在诗意的戏剧中,我们才有闲暇重新审视文学之于当下的价值。
必有人重新思考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有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每年我们都试图从中找出隐匿的规律,却总是不得要领。相对的,另一具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奖项布克奖的评选标准就一目了然,可以简要概括为“好看、可读”,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就获得过此奖,却无缘诺奖。其中的逻辑是,布克奖创立之初所考虑的受众群体就极其精准,多是身为中产阶级的上班族,他们每日火车通勤中的文学阅读,会成为奖项的热门人选。
此前美国的《巴黎评论》文学杂志曾分析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里获奖者的写作特征,锁定了一些疑似标准的关键词:理想主义(idealism)、传统(traditions)、当代(contemporary)、伟大的(great)、现实(reality)、现实主义(realism)、宇宙(cosmos)。
关于理想主义,在之前一次线上预测活动中,参与嘉宾都表示,这一基于创立者诺贝尔本人喜好的标准过于虚幻,早已不再作为考量的决定因素。实际上1902年诺奖第二次颁发时获奖的《罗马史》作者特奥多尔·蒙森,1912年得奖的德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霍普特曼,1948年的获奖者T·S·艾略特……都称不上所谓的理想主义,相反,凭借《西线无战事》获得世俗声望的反法西斯作家雷马克的理想主义却被诺奖无视了。
再来看今年的得主约恩·福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奥尔森是这样评价他的,“尽管福瑟和他的文学前辈们一样持有某种消极的文学观点,但他并未对世界抱以虚无主义的蔑视——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充满了温暖和幽默’。福瑟勇于面对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焦虑,这是他在公众中获得非凡认可的原因。”显然,福瑟与诺奖的初心契合了。
那次线上讨论也再度就村上春树的陪跑缘由达成共识:问题所在恐怕并不是他过于西化的表达,而是有关文学自身的标准,“一方面他想要沉重地对世界历史进行反思,而另一方面,却又把它跟娱乐化的大众语言相结合,以迎合公众的趣味。这显然不是诺奖的路数和方向。”
回看诺贝尔文学奖始于上世纪初的历届赢家名单,尽管人们时常会感到意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探寻人与他所处世界关系的文学本身才是奖项的终极考量标准,似乎在这一点上人们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会太失于偏颇。有一个普遍的观点:从2017年石黑一雄“极具情感力量地揭示了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到去年以“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而获奖的安妮·艾尔诺,再到今年“为不可言说之物发声”的约恩·福瑟,近年来的诺奖变得比较“回归传统”,即文学最初的传统——人学。而从人内心的思维活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出发,正是文学最纯正的面貌。
时至今日,文学的阅读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主义者的理性视角,而更多是普通读者的代入式体验,他们要从中找寻自己,获得共鸣。正向解读作为年度公共文学事件的诺贝尔文学奖,它实则是为文学走向大众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得以了解世界更多样化的文学样态和文学前沿的模样。读者会在阅读中重新认知文学的价值,而作家们也将从中思考写作的使命。或许正因如此,约恩·福瑟才会在获奖后首先做出那样的回应:“我认为这是对文学的奖励,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其他考虑。”
来自北欧峡湾村落的文本宇宙
“很久以前,一个小男孩骑着一辆蓝色女士自行车艰难地踩在乡间小路上,他乌黑的长发在风中飘扬。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个有头发的孩子’是约恩·福瑟。他可能手里拿着吉他盒去乐队练习,或者,也许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去离峡湾和海浪不太远的地方。空气中可能有轻微的毛毛雨。在斯特兰德巴姆(Strandebarm),人们要么骑自行车进入峡湾,要么沿着峡湾,在一条蜿蜒穿过农田的道路上,经过小农场、教堂、青年俱乐部和公共汽车站。约恩·福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上半叶在斯特兰德巴姆长大,他有一辆自行车,一把吉他,感觉像一个艺术灵魂,还有当地每个人都见过的男孩最长的头发。”
2019年,挪威的一本《音乐与文学》杂志在一篇专访中描摹了约恩·福瑟的童年,他出生的村落斯特兰德巴姆,以及后来定居的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成为他的创作原乡。每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的文学故乡,他的创作由他曾经的生活塑造。要了解约恩·福瑟,就需要去往北欧挪威的峡湾。
对北欧文学情有独钟的上海作家陈丹燕曾经这样描述挪威的自然景致:“可以看见冰川融水冲刷大地,雪化了以后会有新的峡湾出现。在那里,会觉得我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生物,是自然当中的一环。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人是有命运的。”福瑟笔下那些生活在此处的人物,面对面前宏大的秩序,无从把握的命运力量,内心自然会生出无力的挫败感和忧郁的情绪,而这也成为福瑟文学的基调。尤其在他的戏剧世界里,人们远离繁华都市,或来到乡村试图寻求新的开始,或终其一生都在乡村度过……难怪他的两本戏剧集的中译本译者邹鲁路,会评价他的作品为“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她选择了大海、雨、秋、悬崖上的老房子等关键意象,作为他作品的入口。如此便也理解了他文字中的诗意暗涌和对时间荒原上相遇之人的悲悯之情,那是孤独静寂的氛围里才能感知的人生倾听。
易卜生奖评委会曾经给予约恩·福瑟这样的授奖词:“他创造了一个自成一格的戏剧世界,他是一个宇宙、一片大陆,自他居住的西挪威延伸至亚洲、南美、东欧和世界其他区域。”而他本人也在创造一个来自北欧峡湾村落的文本宇宙。在《纽约客》2022年的访谈中,他提及了自己的小说“三部曲”和“七部曲”系列。两个系列拥有名字相同的主人公,相同的生活地点,而即使在同一部小说里,主人公也可能身处不同的平行时空。比如在《七部曲》中的一个场景,年轻的阿斯勒望向窗外,一辆汽车正开过,坐在驾驶座上的是年长的阿斯勒,他正带着他的画去往卑尔根……约恩·福瑟像是将他的人物看作声音,某种声音、关联的声音,形成合唱中不同声部的和声。“你得给每个文本创造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跟我所说的宇宙相关。我在创造一个宇宙。”
在他看来,“七部曲“是一个宇宙,“三部曲”则是另一个宇宙,同时,它们又彼此联系。“我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名字,地方也差不多是同一个,主题也是重复出现的。人们会从窗子往外看,通常是往海或峡湾的方向望去。这有点像一个画家在画另一棵树,因为有很多人已经画过了,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画。而且通常情况下一个优秀的画家也会一再重复相同的主题,虽然每次的画是新的。我希望我也这样。”毫无疑问,约恩·福瑟也契合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宇宙”。
约恩·福瑟的文学创作基因
约恩·福瑟曾多次形容自己的内心是一位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句子的节奏尤为重要,它们与内容交织,形成他文字的独特风格。在2022年第二次获得国际布克奖提名后的一次采访中,他曾全盘托出了那些塑造了他一生的书籍,而这其中的第一本,就是奥地利表现主义诗歌先驱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他的诗陪伴他超过半个世纪。两三年前,他曾翻译了他的一本诗集《塞巴斯蒂安在梦中》,今年又出版了《挽歌》的译本。
研究一位作家的文学阅读谱系是有趣的,其中也暗藏着作家自己的风格取向以及他的文学创作基因。在福瑟钟爱的作家中,颇有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辈。其中包括法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短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前者的《喧哗与骚动》,花费了他相当多时间来阅读和理解,书中的写作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独特阅读体验令他受益终生;而后者贝克特的戏剧也一直陪伴着他,《有人将至》可以看作是对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抵抗式回应”。
弗朗茨·卡夫卡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诺奖“遗珠”,也对福瑟产生了超越文学的影响。在他看来,卡夫卡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以此改变了世界;而他真正爱上伍尔夫的小说始于《达洛维夫人》,阅读的感觉“就像她只是把歌词扔出去,每一个都准确地落在了它们应该以优雅的动作作为你能要求的最美丽的文学音乐的地方。”他对于文学的理解便是在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才真正形成的。
他还透露了自己将卡夫卡的《审判》和另一位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德·穆南的《大平原》翻译成了挪威语译本,巧合的是,在此次诺奖评选中,作家穆南与福瑟的名字比肩出现在博彩公司的赔率榜上。而对于这位澳大利亚作家,福瑟特别评价说:“我俩的写作路子不同,但我可以判断出来我们有些观看事物的方式是相似的。”
即将纷至沓来的新译本
约恩·福瑟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有关他的作品的中译本的出版也提上了议程。实际上,目前约恩·福瑟已经出版的中译本,仅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出版的两种剧本集《有人将至》和《秋之梦》。福瑟夺奖后,早有人第一时间去官微“道喜”,然而,上海译文的回复却称,版权早已过期,并提醒读者“敬请期待友社推出新书”。
“友社”所指,自然是今年的“大赢家”译林出版社和世纪文景。据译林出版社透露,他们“自2016年就开始洽谈,经过数年的反复沟通与互相了解,于2022年经过竞价,才敲定了重要作品《七部曲》的版权,又在几个月后顺利加购《晨与夜》的版权,另有其他戏剧作品也在洽谈中。”
必须提及的是,自2007年的多丽丝·莱辛之后,译林长达多年与诺奖得主的重要作品无缘,除去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成为古尔纳获奖前国内唯一收录其作品的著作。如今,正如豆瓣一位书友所言:“约恩·福瑟这题的感觉就是,这个不难猜。但敢出手能拿稳的,都是钱包鼓、根基深的出版机构,毕竟剧作集真的不好卖。”
相比之下,福瑟的获奖将世纪文景的命中率进一步提高到“五年三中”——彼得·汉德克、露易丝·格丽克、约恩·福瑟。不过,尽管约恩·福瑟的两个译本的PDF版已经在各微信群流传,他的带动效应却还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