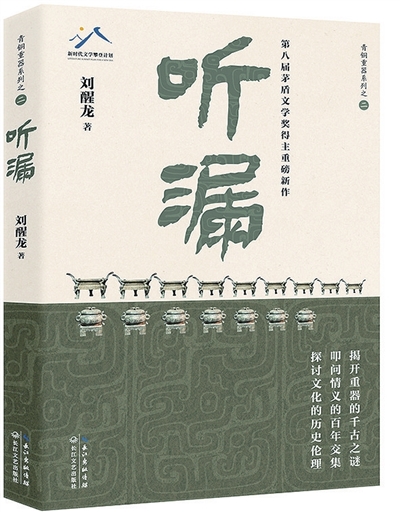
《听漏》 刘醒龙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2014年作家刘醒龙出版青铜重器系列之一《蟠虺》时,考古这行还比较冷。“小说着重表现的曾侯乙尊盘,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几年,忽然变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的确,“博物馆热”在近些年越来越热,今年暑期热出了圈,甚至炒出了“黄牛票”。与其在热闹中匆匆忙忙浏览博物馆,不如先冷静下来读读书,在了解文物之后,再去博物馆里细品。读书,是亲近文物、了解历史的一种很好的途径。正如刘醒龙所言:“还是那句俗话,文学的作用是无用之用。”
“在历史面前,最能体现王者之气的青铜重器非鼎簋莫属。在辉煌的朝代,青铜鼎簋会让这种辉煌更加灿烂。在衰竭的王朝,青铜鼎簋会将这种衰竭衬托得更加残败。”刘醒龙家离湖北省博物馆距离只有一站地,他进去参观过无数次。偏偏2004年那一次,被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认了出来。那位工作人员自告奋勇,领他去看摆放在角落里的曾侯乙尊盘。 这一看,刘醒龙被曾侯乙尊盘迷住了,从此开始全方位留意这件“国宝中的国宝”。
10年后的2014年,他出版了以曾侯乙尊盘为素材的长篇小说《蟠虺》,2024年,刘醒龙的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听漏》问世。小说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历史演变结合起来。
完善人的精神生活
《听漏》中写道“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刘醒龙认为,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如果换掉关键词,说“以文学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接下来的话也是成立的。“写考古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例外。”
《听漏》涉及了很多考古和文物知识,“知识不等于文学,文学必须有知识涵养。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写考古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那么也就无法例外。”
在刘醒龙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工作者非常接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看似无中生有,其实字字句句都是有的放矢。考古工作同样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从田野调查到打探方、挖探沟,一旦找到遗存,就像写作时的下笔如有神助,小的遗存如写短篇,大的遗址如写长篇。”考古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那些人人心中都有、个个笔下全无的状态,在一般人眼里百无一用,却被作家写成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典。考古工作与文学创作的缘起,在‘无中生有’这一点上,实在太像了。”
用“听漏”二字作为书名,刘醒龙的解释首先是其音韵的魅力,还有它蕴涵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我用感官发现了历史的破绽和现实生活的破绽。书中有一段话说,‘漏水的地方总漏水,不漏水的地方总不漏水。就像贪官到哪里也要贪污,清官到哪里也是青天,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听漏的意义,也是要听人和听事。”
感受青铜重器的激情
以青铜重器为写作对象,是刘醒龙20年前起的念头,当年的考古和文物,几乎进不了社会上的话语体系。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讲究的是沉淀积累。“在文学界,极少有将热度一点也不减的事物及时写成作品而成为经典的。即便有灵感,也需要像种子一样埋藏在沃土里,等待时机生根发芽,经过季节的考验,才能开花结果。很多时候需要将一颗冰冷的种子放在心里,一点点焐暖焐热,经过漫长的滋养,才能得到想要的收获。”这份收获,在《听漏》体现为“不少人物都超出原来的设计,硬是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之路。我很惊讶,但也明白,这说明《听漏》中铺垫了足够的沃土,供给他们独立自由地生长。”
“人们早已熟知曾侯乙编钟,后来又熟悉了曾侯乙尊盘,藏在博物馆幽深处的九鼎七簋迟早也会被人熟悉,熟悉与不熟悉的青铜重器,面孔看上去无一不是冷冰冰的,实际上,激情才是它们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刘醒龙在《听漏》的创作谈里写道: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别的什么人,能够感受到藏在它们身后的激情是一种幸运。生活之于文学也是如此,可以说激情需要扛起一座大山,也可以说激情能够怀抱一片大海,还可以说一个人的激情纵然达不到面向整个人类,至少也是一个族群一个社会的理性与感性的共振。激情贮存在我们的骨子里,唯有真实可感地承担和行动,激情的能量才有可能爆发。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贾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