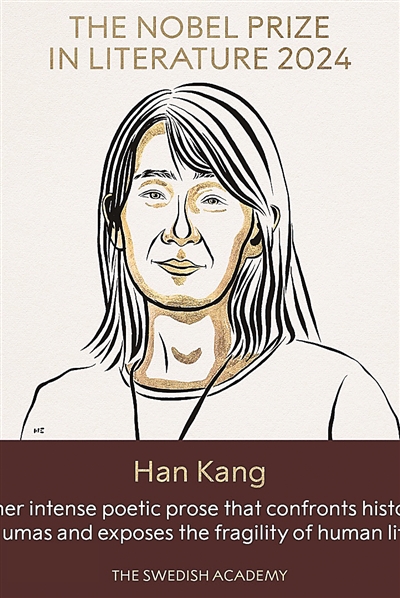

■获得2024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女作家韩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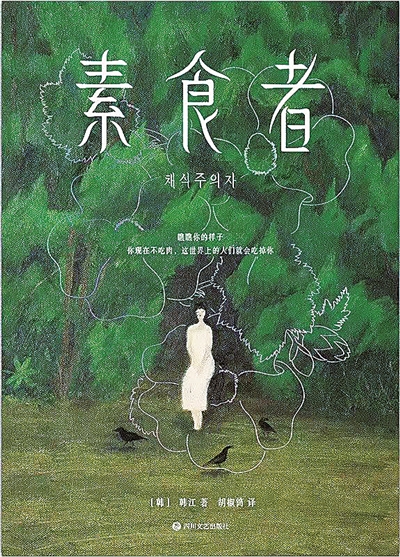
《素食者》
(韩)韩江 著 胡椒筒 译
磨铁/铁葫芦/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版

《白》
(韩)韩江 著 陈允然 绘
胡椒筒 译
磨铁/大鱼读品/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版

《植物妻子》
(韩)韩江 著 崔有学 译
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版

《把晚餐放进抽屉:韩江诗集》
(韩)韩江 著 卢鸿金 译
磨铁/铁葫芦/九州出版社2024.01

《失语者》
(韩)韩江 著 田禾子 译
磨铁/铁葫芦/九州出版社2023版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当瑞典文学院将202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国女作家韩江,此前所有赔率排名似乎都脱离了正轨,正如出版界普遍的共识:自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因评委舞弊丑闻停颁一次以来,各种有关该奖项的赔率榜预测便丧失了参考性。
然而,韩江折桂绝非爆冷,而是基于一位语言风格与创作主题鲜明并一以贯之、不断革新的中年女性作家的水到渠成。这位“70后”作家对于当今文坛并不陌生,早在2016年,她已凭借小说《素食者》斩获了国际布克奖,那一年被她击败的对手包括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晚年代表作《水死》以及另一位本届诺奖的强劲候选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终曲《失踪的孩子》,最终韩江从154名候选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奖项历史上第一位亚洲作家。
此后她连续获得国际奖项,2017年,获得了有“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马拉帕蒂文学奖;2018年,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并且创纪录地在同一年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2019年,她获得西班牙圣克莱门特文学奖……
这一次,韩江依然创造了纪录。54岁的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女性获奖者,最年轻的获奖者是1938年的诺奖得主赛珍珠,当年她只有46岁。无论如何,韩江的获奖就像是诺贝尔文学奖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标识——脱离了之前类似于终身成就奖的盖棺定论式“老迈”气质,从对宏大主题的青睐,转向对于微观社会人生命题的观照。而女性作家的比重也在继续增加,从2018年至今,七届诺贝尔文学奖中,有四届都颁给了女性,在此之前的100多年里,总计仅有14位女作家获得过该奖。无疑,韩江也是她们中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女性。
出版界并不陌生的文学“韩流”
韩国女作家韩江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早在2013年,其代表作《素食者》已推出中译本,名为《素食主义者》,国内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位70后韩国女性作家。“磨铁”于2021年推出新版《素食者》,随后,又出版了《白》《植物妻子》《失语者》《不做告别》,今年又有韩江的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面世。
而韩江在国际文坛的风生水起也绝非偶然的个例。如果关注一下韩国文学过去十年在国际书展上的表现就会发现,自2015年起,韩国作家开始频繁现身各种国际文学场合,仅当年的巴黎图书展,就有30位韩国作家受邀出席。韩国文学账号GoodbyeLibrary主理人、长期关注韩国文学的编辑叶梦瑶观察到:整个韩国文学销量的转折点是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此后慢慢进入大众视野并引起较多关注的韩国文学作品包括韩江的《素食者》、80后天才女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以及去年出版的另一位80后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据粗略统计:从2019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每年出版的韩国文学在30本左右,大陆地区2019至2021年,一直是每年出版10本左右,在2023年急速超过40本。
韩国文学热潮的背后是诸多来自官方的推力: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下属机构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和文学翻译院从2015年开始积极实施韩国出版产业“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海外市场。译作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让韩国文学在各类国际奖项中大放异彩,2016年,韩江的《素食者》斩获国际布克奖,应与此文学战略的推力密不可分。
目前,韩江的简体中文版权大部分都在“磨铁”手中,“磨铁”也被看作是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赢家。2019年,正是“磨铁”引进出版了《82年生的金智英》,成为韩国文学在国内的“引爆点”之一。在“磨铁”的出版计划里,韩江以光州事件为背景的长篇代表作《少年来了》,以及另外两部小说新作《黑夜的狂欢》《伤口愈合中》都已囊括其中。尽管国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期待已经式微,但它所带动的文学类图书出版与销售依旧堪当风向,而韩江,也必然引发新一轮文学阅读“韩流”。
极端的故事质问人间复杂的格斗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院教授崔一,曾经概括对比中日韩三国的文学特征:韩国的美学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绝对性的价值取向的,比如追求悲壮美、崇高美、神性美等等,相对中国文学一直以来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的终极关怀、日本文学具有的强烈的自然关怀,韩国介于两者中间,更倾向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恐怕也正是一些韩国文学作品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而在韩江的小说创作中,所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摹,实则已上升到关于人的本质的探寻,正如毛姆所认为的,“小说的终极意义是揭示世界的本质”,韩江则持续思考着人的本质的命题,“写《玄鹿》时我就想,人是什么,人就是和玄鹿一样的存在吗?我写第二个长篇《你那冰冷的手》时,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的脸是什么?人的脸是不是假面,人是不是生活在假面中所以才会孤独。我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素食者》时,思考的是人能不能完全地去除暴力,能不能在去除暴力的状态下生存下去。写第六部长篇小说《少年来了》也是问同样的问题。”韩江形容自己的作品是在“质问人间的复杂格斗”。
作为最被读者熟悉的作品,《素食者》无疑是韩江小说美学的典型范本,它讲述了一位为了逃避来自丈夫、家庭、社会和人群的暴力,决定变成一棵树的女人——英惠的故事。小说共分为三部分:“素食主义者”“蒙古斑”和“树火”,分别以英惠丈夫、姐夫和姐姐的视角讲述,暴力、欲望、占有、抛弃,每个人对待英惠的方式不同,但同样自私且粗暴。在英惠的丈夫郑先生眼中,“病”前的英惠,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不高不矮的个头、不长不短的头发,相貌平平,着装一般,温顺、平淡、文静。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英惠完美地扮演了平凡妻子的角色——料理家务,伺候丈夫,就像千千万万的传统妇女一样。然而,一场噩梦之后,妻子却突然开始拒绝吃肉,拒绝为家人准备荤菜,甚至开始拒绝自己的“人类”身份,把自己当成了一株植物,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谢绝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随着反叛愈演愈烈,丑闻、虐待和疏远开始让她螺旋进入幻想的空间。精神和肉体的蜕变让她远离了曾经为人所知的自我……最终她放弃了所有食物,放弃了作为动物的本能,也放弃了语言和思考,真正活成了一棵树,只要水和阳光。
“通过这么极端的故事,我感到我可以提问最难的人性问题”,在国际布克奖颁奖礼的致辞中,韩江说:“我在写作时,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英惠的故事指向每一个试图冲破固有规则,活出自我的女性,她们以柔弱和静默与现实对抗,期待一个植物组成的纯真世界。韩江刻画了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规则的女性形象。
成为植物这一带有荒诞感的描述是一个隐喻,意味着远离人间的争逐与枷锁,摆脱无形的暴力和黑暗,正如这本小说的英译者黛博拉·史密斯所追问的那样,“我们能否忍受一个暴力和美丽混淆的世界”,韩江要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探索创造一个美丽纯真世界的可能性,这不仅是《素食者》,也是她一切小说写作的动力。
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言,在小说里,她只是提问,却无法提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写作就像是点燃火柴,在一旁凝视火苗燃烧,直至熄灭。也许这就是小说所能做的一切。就在这凝视的瞬间,向人类和人生提问。也许,我就是在完成一部部小说的过程中推动着我的人生前进。”
充满“诗意”与“实验性”的戏剧文本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给予韩江如是评价:“她以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并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官网称其“对肉体与灵魂、生与死之间的联系有着独特的认识,并以诗意和实验性的风格成为当代散文的革新者”。要真正理解她作品中的“诗意”与“实验性”,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或许是一个合适的文本。
在这部小说集中,收录了八部作品,尤以《童佛》与《植物妻子》为典型,红、白、黑、绿四种色彩依附于不同意象,频繁出现在作品中,以此隐喻人物的心理及情感,她以家庭、婚姻、爱情为切点,在色彩明暗的对比与更替中,将一场遭遇重重困境的女性追寻自我之旅展现在读者眼前。而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植物无疑是诗意的载体,韩国评论家黄桃庆在书后的“解说”中,专门以“脱身或向往植物的憧憬”为题做了专门解析——
《植物妻子》中,女主人公不愿像她母亲那样出生在海边贫困村又死在那里,因此远离故乡,却因为爱上一个男人定居了下来,相信爱情也可以到世界尽头,但爱情却渐渐消失:曾经被她的嗓音迷住的丈夫最后连她的嗓音和呻吟声都听不懂,妻子的独白无法传达到丈夫那里,当妻子讲述去天涯海角的梦时,丈夫却在讲花草的事情;丈夫国外出差从“远处”回来时,妻子却站在阳台梦想着逃到“远处”,但铁制大门和阳台的铁栏杆所象征的“看不见的锁链和死沉的铁球”拘束着她的腿脚,使她动弹不得。当妻子说的“去远处”的那句话被埋没,她逃脱的欲望受挫时,她干脆失去了双腿。牙齿掉落,找不到一丝“两腿直立动物”的痕迹,就这样逐渐变成了植物,然而她却因此脱去了动物的身体和欲望的身体,向植物的变身成了一种新的逃脱方式……据说这篇小说也是后来获得布克奖的《素食者》的文本前身,其创作缘起都来自前辈韩国作家李箱笔记中的一句话: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
黄桃庆说:“在痛苦和创伤的尽头见到的这一植物的世界,是抛开欲望的、绝对顺应的、被动的世界,韩江作品中人物反而在那里向自由飞翔。”最终,“花终于穿过束缚着她的阳台天花板,又穿过屋顶的钢筋混凝土一直伸到楼顶向天空伸展。花不是静止的、软弱而被动的存在,而是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向天空伸展的生命的实体。现在这花能够自我梦想,自我行动,自我生存。”
《童佛》则是讲述把刀转换成花的过程的故事。故事的结尾,主人公来到森林,领悟到“每根树叶都向外剑拔弩张的”那些松树现在已脱下那份锐利,就像刚刚钻出来的新芽一样泛出浅绿色。终究还是柔软战胜了尖锐,春天战胜了冬天,植物战胜了铁器。这就是生命的力量,也是作家韩江所梦想的植物的世界——它和光同尘,充满诗意的戏剧性的荒诞与残酷,却又真实诉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以静水深流的诗意文字,拥抱创伤
韩江出身于书香世家,她的父亲和两位哥哥都是作家,14岁时她便清楚地为自己明确要以写作为一生志业。而对于自己如何走上写作之路,她亦曾有过确切的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独裁和军部统治结束的时期,从那时开始,在韩国文学界,讲宏观的、社会性的作品没有市场了,作家和读者都更注重探索内心的、个人的东西。1993年,我发表《红锚》登上文坛,算是从‘作家揭露社会’的强迫症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代作家。当时出了不少年轻作家。”之后,她发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慢慢发生的嬗变:二十多岁时,曾经经历的“光州暴乱”对她的影响依然很深,那时的她在每篇日记中都写上两句话:“现在能拯救过去吗?”“活着的人能拯救死去的人吗?”这或许也是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涉及暴力的原因。
评论界这样评价韩江的文字:“给人以直透灵魂的情感冲击,犹如一把鲜血淋漓的剔骨刀,又有着宛如梦呓的恐怖诗意。”而即便是透露出如此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言,却几乎读不到热烈慷慨的生活,在她笔下,“一切都是静水深流,人物在冷峻的描写中各自缝补着自己破碎的内心世界——尽管有时候,这种‘修补’是以几近惨烈的方式达成的”。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相信,人类的心灵创伤,与其说需要被‘疗愈’,还不如你张开双臂去拥抱。悲伤是人类心中摆放死亡的空间;当我们不断去探访那些空间时,我们在默默地、痛苦地向悲伤敞开怀抱。而在这样自相矛盾的过程中,生活也许才变得可能。”
小说家庞余亮和钟求是曾在2020年进行过一次有关《素食者》的对谈,二人不约而同地感受到韩江语言的安静性,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英惠的少言轻淡一样,收敛而平实。英惠被父亲打耳光后用刀子自伤,之后在医院又把上身裸露于众人目光里,这些戏剧性情节的讲述中,作者的情绪依然稳定,没有大惊小怪的弹跳腔调。其中的一段发生在病房里的对话,“英惠把消瘦的脸凑过来,透露重大秘密似的说道:‘我现在不是动物,姐姐。’姐姐说:‘你在胡说什么啊?难道你真的觉得自己变成了树木?植物怎么能说话呢?植物怎么能思考呢?’英惠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一丝不可思议的微笑绽放在了她憔悴的脸上:‘姐姐,你说得对……不多久,语言和思维,都会消失的,很快!’然后英惠嘴里发出哧哧的笑声。”(据2013版)在这里,他们认为:韩江最后选择的语言是树的语言,一棵树站在那里,给人的感觉就是静默与孤独的,尽管它的内部生长着野性。
这又让人想到小说的英译者黛博拉·史密斯的评语:韩江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她所写的内容通常很极端,大都充斥着极端的暴力和戏剧冲突,但她的语言从来不是大喊大叫的类型。她的笔法自控,但不是纪实报道式的冷漠,“我觉得,她对过度煽情和冷眼旁观之间的平衡把握得刚刚好。”
那次对谈中,庞余亮和钟求是还对比了韩国70后作家和中国70后作家,他们似乎有不少共同的关注点和思考点,比如:“对当下人们内心困境的重度拷问,对世俗秩序的抵挡与逃离,在喧闹的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学之旁,顽强地保留着沉静的纯文学性格”,但他们又不同,“单从韩江的《素食者》就可以看出,韩国作家的写作思想更解放一些,也更自由一些,他们能把想象的边界推得挺远,并且对人性的根部挖得挺深。在这方面,中国的同代作家应该注入一些勇气,更用力地打开自己、挤榨自己。”另外,他们还提及她作品中的若干细节,如《素食者》中父亲杀狗与喂肉,姐夫画画的描写,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呈现,同时这也是小说家才华的显现之处。于是他们想起作家王安忆说过的话:现在的小说家越来越不讲究细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