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艺术家 Maggie Stephenson的女性题材作品

《最好朝南》 三明治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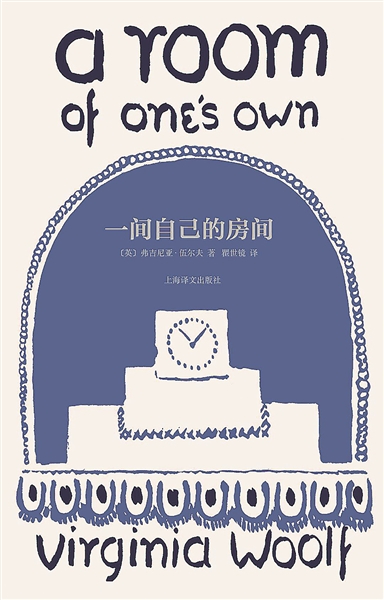
《一间自己的房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瞿世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雪春秋》 郑在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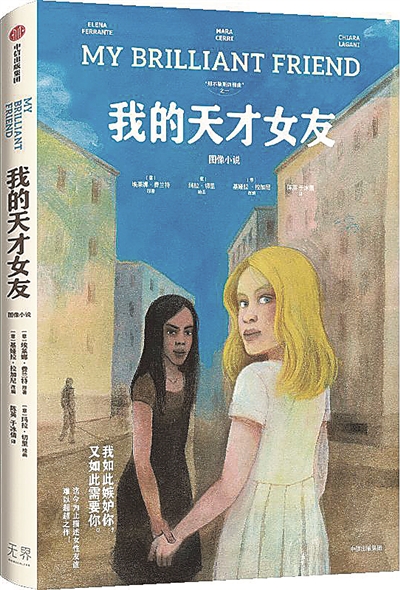
《我的天才女友:图像小说》 (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 (意)玛拉·切里 绘 陈英/于冰倩 译 中信出版社202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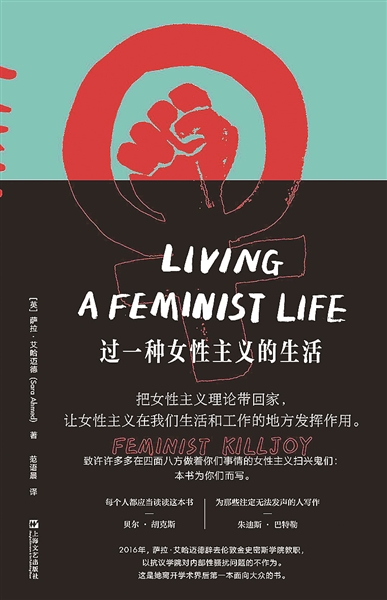
《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 (英)萨拉·艾哈迈德 著 范语晨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10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上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她描述了一种女性理想: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
同样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世界的东方,另一位女性作家丁玲也以一部散文式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打破女性的沉默,她塑造的充满感情苦恼、性格矛盾的知识女性莎菲,背负时代的苦闷和创伤,最终选择忠于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她被看作是“后五四时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初声。
伍尔夫描述的女性理想生活,在100年后仍未过时,依然是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女子一生的追寻,而莎菲的情感困顿和叛逆,仍是当下生活洪流中女性精神世界的难题。最近TVB新剧《新闻女王》引发的热议足以表明,女性精神之独立的行动与表达不仅从未终止,且已成为大众热衷的公共话题,剧中真正引人入胜的不是女主们的职场战斗力,而是她们殊途同归的独立意识和他人能奈我何的那份自我掌控的笃定,那句“找个男人嫁了吧”,无异于对当代伍尔夫和丁玲们的极端羞辱,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2023年,女性主义潮流先锋伍尔夫的新版系列作品,始终高居网络人气榜的前端,令作家丁玲一鸣惊人的女性觉醒之书初版近百年后又再度现身。
这一年,我们对于女性的理解和观照深入、具体,涉及日常,从虚拟到现实,从文学到科学,愈演愈烈。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位女性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她的代表作之一《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的百年旅程》中文版也在这一年面世,书中首次全面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探究不同代际的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阻碍的演进,以及被疫情极度放大的两性差异。
社会公众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女性,人们深度探讨和理解女性处境,记录那些曾经羞于言说或被有意无意忽略掉的私密经验。如戈尔丁所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生活写作者”的非虚构表达欲
12年前,曾经的媒体人李梓新为大众写作者创办了一个名为“三明治”的写作平台,聚集非“科班”出身的写作“素人”。他发现,这些写作者中,80%以上是女性,她们大多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充满着对自身经历和生活的表达欲。
她们描摹女性隐秘而细腻的情感,在家庭中、生活中的曲折,甚至那些无法言说的私密,将压抑心底的困顿公开——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晓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吗?比如盆底肌;养育了3个孩子的22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长期遭遇家庭暴力,靠自己能离得成婚吗;随先生搬到陌生城市,事业停滞,顺势成为“家庭主妇”是应该的吗;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中说:女性不被看见的残酷事实和代价,存在于每一次凝视,每一趟公交,每一间厕所,每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存在于你我日常生活的每一处隐秘角落。而女性写作带来了一种亲切感,一种彼此相连的感觉,让我们对“被看不见”“被消失”的女性社会身份保持更敏锐的觉察。
这或许就是“生活写作”的意义,它包含了家庭、爱情、友谊、孩子、以及历史是如何作用于个人身上的等等不同维度的主题,让女性的发声有明确的指向,让生命和生活的日常随文字流动,所有人成为命运共同体。这也是我们今天依旧在读伍尔夫和丁玲的意义,写作让生命有了容器,和他人“碰杯”。
行至2023年,倡导“生活写作”的“三明治”平台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推出了女性非虚构写作合集《最好朝南》。22位女性书写者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生命故事,境况与细节各异,但女性的发声终于回到了大众最本原的土壤,如书中所说:如果用一把够长的匕首去划开不同境遇的表面,猛力扎向深处,就会看到,作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此相似。
《最好朝南》回应了100年前的伍尔夫,她们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开始写出自己的故事,并对这间房间提出了舒适度的更高要求——最好朝南。
女性小说家虚实相抵的时代感
相对于《最好朝南》中非虚构女性写作者的自我宣泄,一个女性小说家的书写往往虚实相抵,充斥着更具情感张力的戏剧。
比如在2023年倍受媒体关注的女作家辽京,她说:写作是表达的出口,也是一种观察、梳理当代生活的方式。在2023年,辽京的新小说集《有人跳舞》出版,延续着她对女性、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感性观照。当被问及女性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所谓“第一性”的男性有什么不同时,她的回答是:我们更关注人的情感,尤其是落寞的情感,我们和那些人间的失落者更有共鸣。《有人跳舞》中并不只有女人,有关男人,有关困境,有关暴力,有关亲密关系。辽京在21世纪20年代对于女性身份自发的关切,似乎正与女性之于时代的关联同频,她的成名作《新婚之夜》,被看作是这一时期随国内女性主义浪潮应运而生的“一部当代中国女性困境启示录”,而今年面世的《有人跳舞》,则在讲述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的同时,更加紧凑地展现女性暗涌的内心、自我意识的觉醒。精短的小说里,那些逃离的女人、困惑的女人、痛苦的女人、解放的女人,在绽放,在败落……她们是虚构中现实的存在,也是时代观念的缩影。你能从日常中指认出她笔下人物的影子,又能从她们身上挖掘出浓缩的荒诞。
“小说不是一条道路,更像一所房子。”作家艾丽丝·门罗的这个比喻,辽京很喜欢,她说她的小说也是在“建一座房子,天冷的时候,路过的人可以自由地走进去取暖,休息然后离开”。有网友把她的小说《暴雨内涝》里关于失业的段落摘下来,感叹这就是自己失业的状态,引发了网上对于失业话题的讨论,还有读者在见面会上向她诉说平时绝口不提的生活和情感困惑……这些都让辽京感到惊喜,因为在她看来,小说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能形成一片同温层”。
关于写小说的意义,另一位青年作家郑在欢,在她的首部长篇《雪春秋》的后记里也有表述:“她们没法被概括,或许正因如此,才需要小说吧。”《雪春秋》讲述了三位来自农村的女性三十年间的成长经历。残缺家庭带来的责任、荒谬的婚俗、牢固的偏见,都在阻止她们打破外在的限定,成为自己。这些被迫早熟的女孩,为了不再受困于童年和家庭,成为外出的打工者,不断经历挣扎与失败,终于为自身搭建了一个安全的空间。
郑在欢表示,她写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戏剧家彼得·汉德克,他在《无欲的悲歌》中,曾用寥寥5万字,以碎片化、论断式的笔触写了他母亲的一生,只聚焦于母亲被时代洪流淹没时的感受。这给了女作家一点启发,“我之前写小说,是不写心理的,我只写动作,觉得故事情节会说明一切。而汉德克以感受、不以故事出发来写作,甚至可以说,他极度痛恨故事。”在读完《无欲的悲歌》后,郑在欢采用了感受+故事的写法,这一对她而言全新的写法,使人物变得更加立体真实。
虚构的情节中也充满了现实感的设定,小说中的女性并没有获得关于女性觉醒的认知,更没有导师引领走出自己人生的困顿,她们就如同现实中任何一位成长中的女子,获得成长最真实的方式,是通过与世界的肉搏,在与生活的对撞中自强。
这或许是写作为女性带来的另一剂良方,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人都是庸众,没有先知的视角,只有在各自生活的狭小土壤里不断野蛮生长,做出偶然的选择,在有如西西弗斯那样的无力感中感知生活,而小说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她者”,比如主人公秋荣,她所做的抗衡就是拒绝每一个具体的选择,并具有敢于承担其代价的果敢。
一名知识女性的文学自证
在2023年还有一部小说以图像小说的方式重归大众视野。那就是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过去的十年里,“那不勒斯四部曲”可能是世界范围里被最多人阅读的严肃文学作品了,由它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也已播出了三季。
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命运交织缠绕一生的女性,背景设置在充满混乱和暴力的那不勒斯小城。前半部分,充斥旧式的意大利“家族感”,后半部则是关于女主人公如何从家庭里一点点分离出来,最终变成孤身一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得到自由。小说的叙述者莱农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通过不断获取知识、进入更高的阶层来覆盖令她蒙羞的贱民身份,冲刷掉年少时的穷困和无知。而她在童年时就认识的朋友莉拉一直激励着她。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推动力。她们时而走近,时而远离,时而相助,时而为敌。费兰特曾在她的书信采访合集《碎片》中这样概括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她们一个从另一个身上获取力量。但要注意一点,她们不是总是相互帮助,她们也相互洗劫,相互盗取能量和智慧。”
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莱农,她的反抗和成长是小说十分明晰持续的主题,青年作家张悦然曾为这本小说写下导读,在她看来:费兰特笔下的莱农是通过书写一本思考女性存在意义的书,突破了写作的瓶颈,实现了表达上的自由。同时,她通过与尼诺分手,摆脱了他对自己的影响和干扰,从而确立了个人的价值。她通过与母亲的和解,更为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挖掘了女性身份的意义。而另一位主人公莉拉,就像莱农自己坦言的,如果没有莉拉,她可能会相当沉湎于自己用知识改变了命运、完成了阶级跃升的那份荣誉。是莉拉让她跳出自己的局限,看到了女性生命里那种更大,更悲凉,更无助的东西,莉拉给了莱农追求真实的能力。
《我的天才女友(图像小说)》在2023年的面世,似乎冥冥中也在让我们重新理解与认知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据说,加拿大女作家希拉·海蒂曾在对费兰特的采访中问她,为什么在包括“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内的很多当代女作家所写的作品里,女知识分子的形象总是不大可爱的那一个,她们好像自身缺少某些东西,需要另一个底层的女性为她们提供。
费兰特的回答颇耐人寻味,她说:“或许是我们女作家对于女性可以很好地运用思想,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我们的想象总是有限制,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更完美的女性形象,放在那些不那么多使用思想的女人身上。”或许这同样也是当下的我们对于女性的一种无意识的偏见和误读。
身为女作家,费兰特在讲述女性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也在挖掘一种独属于女性的语言。还是在那部《碎片》中,费兰特提出,女性要改变文学固有的审美标准和创作观念,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使用自己的语言。要用自己创造的语言去命名、去定义那些尚未被开掘的女性思想,或者尚未被说出的女性体验。
她提到“碎片”这个来自母亲的方言词汇,“那是她经常说的,就是当一个人遭受各种矛盾的情感折磨时感受到的东西,她说她内心一团‘碎片’。这些碎片折磨着她,在她内心东拉西扯,让她头晕,嘴里发苦。这是一种很难说出口的苦,指的是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搅和在一起,就像是漂浮在脑子上的残渣。‘碎片’神秘,会让人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它会引起那些难以名状的痛苦。”令人意外的是,张悦然为此特地请教了翻译家陈英,从她那里找到了一个陕西方言里的对应词汇:“木乱”。
“碎片”一词是否会被认定为一种女性主义词汇,我们无从考证,但费兰特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坚定而清晰,她也曾更加直白地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女性的才华是被浪费的。在这个男性制定规则的世界上,她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一种方式来兑现自己的才华。
成为现实中的“扫兴鬼”和问题制造者
最后要提及的是一位以身试炼的女性主义写作者萨拉·艾哈迈德。2016年,萨拉·艾哈迈德辞去伦敦金史密斯学院教职,抗议学院对内部性骚扰问题的不作为。《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是她离开学术界后第一本面向大众的书。对她而言,理论的表述较之文学,会更加准确、直白且具有力量。
在这本面向大众的学术著作中,艾哈迈德用诗意的语言阐发了身为女人的日常经验、对象、遭遇、情感和具身体验,呈现了女性主义长期以来的工作——发生在街巷、家庭还有工作场所的工作,编织出具体可行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四面八方的“女性主义扫兴鬼们”提供了一份实用的生存工具包。
女性主义者为何总被视作耸人听闻的疯子、没好气的扫兴鬼、烦人的问题制造者?组织为何总是包庇性骚扰、强奸的加害者?不公正的制度为何岿然不动?幸福的承诺为何成了不幸福的根源?性别为何是一种对人之可能性的限制?特权为何是一种“节能装置”?暴力为何总与女人如影随形?……在2023年,许多看似遥远的问题似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艾哈迈德用这本书、用写作这一行动本身,为我们示范了拆除父权制世界的工作,鼓励反抗制度性与人际的不公正,去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激进吗?也许吧,但她却告诉我们:“我们在一点点地拆解,纵然缓慢,但我们的确正在拆解!”
在萨拉·艾哈迈德看来,女性拥有的那间最好朝南的房间,应由女性主义的砖瓦搭建,她将目光投向她女性主义之路上的前辈和同路人:弗吉尼亚·伍尔夫、乔治·艾略特、西蒙·德·波伏瓦、贝尔·胡克斯、奥德雷·洛德、朱迪斯·巴特勒、唐娜·哈拉维、劳伦·贝兰特、格洛丽亚·安扎尔杜阿——她用女性主义前辈的文本串联出一条女性主义继承之路,用女性主义的砖瓦搭建起一幢女性主义住所。
《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既毫不妥协地站在激进的立场上呼吁社会变革,又坦然承认,在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斗争中,我们需要歇息片刻。艾哈迈德切实地宽慰我们:明智地选择自己的战斗,有时你能做的只有那么多,当事情实在太过分时,你可以退出,你可以离开,你可以悲伤。
这个用理论讲女性故事的人,鼓舞我们“一起做一名任性的女性主义扫兴鬼——
我不愿意把幸福当作我的目的;
我愿意造成不幸福;
我愿意支持那些愿意造成不幸福的人;
我不愿意对那些有意冒犯的玩笑发笑;
我不愿意忘掉那些没有过去的历史;
如果包容意味着被纳入一个不公正、暴力和不平等的体系中,那么我不愿意被包容;
我愿意过一种在别人看来不幸福的生活,我愿意拒绝那定义了美好生活的脚本,我也愿意去拓宽它;
我愿意把“hap”(偶然性)还给“happiness”(幸福);
当纽带对自己或他人造成损害时,我愿意斩断任何珍贵的纽带;
我愿意加入一场“扫兴鬼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