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 亡命(1898—1903)》 许知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单读 202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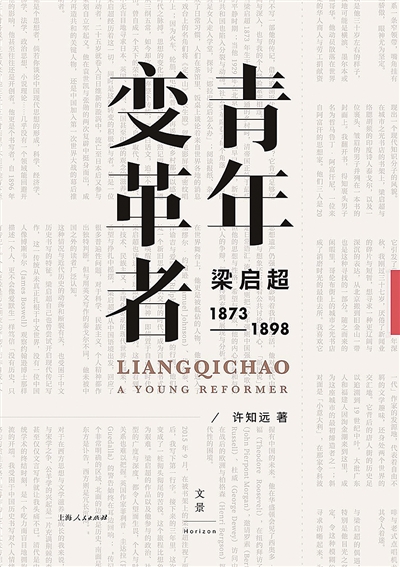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许知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9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怎样去理解一个世纪前、与你的经历迥然的一个人?翻阅《清议报》是一种方式,喝菠萝啤酒、在墨尔本的淘金博物馆中闲逛,也是一种方式。时代充满断裂,过往即他国,也仍有某种连续性,风物会意外地存续下去,每一代的苦痛与喜悦,希望与焦灼,亦不无相通。”单向空间的创始人、作家许知远在他的新书《梁启超:亡命(1898—1903)》中试图以沉浸式的写作方式,重新理解一个世纪前的“70后”青年梁启超。
拟定五卷本的梁启超传记的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日前出版面世,与此同时,许知远的书店单向空间开到了日本东京。两者之间,不无关联。许知远将后者看作是前者的文创周边,又或者,他是在借鉴传记作家罗伯特·A.卡洛:为写作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传记,特别搬到约翰逊的家乡德克萨斯州居住,以体验传主经历的人生。在八月上海的新书分享会上,许知远透露,将书店开到海外,大约也是想切身体验当初梁启超异国创业的艰辛。
1898年,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他从天津出发,乘坐大岛号抵达日本吴港,从东京到横滨,办报创业,在那里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这本书是关于梁启超的海外流亡史:横滨、夏威夷火奴鲁鲁,到新加坡、悉尼,再到温哥华、蒙特利尔、纽约、旧金山……梁启超于颠沛流离中遭遇旧经验与新思想的碰撞,接连的挫败打击并未遏制他蓬勃的好奇心和强大的生命力,令百年后追索他脚步的许知远倍受鼓舞。他在第二卷的自序中写道:“我感到自己的雄心逐渐坚定。我想借由梁启超,写出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国转型的希望与痛苦,并通过一张人物、细节之网,令人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之精神与情绪。”
历史上的梁启超在25岁时被迫迅速成熟,30岁时重新发明了自己,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以及他所经历的转折中的时代,也是在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发现我们自己以及当下的生活。
一个拥有不恰当雄心的传记写作者
从2019年许知远所著梁启超传记的首卷《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面世之日起,他便不得不面对众多的质疑之声。在历史研究领域,关于梁启超的中外专业著述汗牛充栋,作为历史学“民科”的许知远为什么还要写作五卷本如此大体量的人物传记?在上海的图书分享会上,作为嘉宾主持的评论家燕舞开门见山抛出此问。此前香港分享会上,一位读者曾当面表示,因为传记的作者是许知远,阅读之初便已为这本书减去了一分。
而作为传记写作者,许知远并不掩盖他“不恰当的雄心”。他说:我们做很多事情可能都是由不恰当的雄心开始的。”对于传记写作的迷恋始于其青春期的成长教育。许知远首先是一个英语世界传记写作的迷恋者,二十多岁时他接触到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的《凯恩斯传》,他用三十年时间撰写的这部三卷本传记,让许知远重新理解了传记写作的意义:“从中不仅看到凯恩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人生,还有经济学背后一整套的道德理想,审美倾向,他和他的朋友的关系网络,他背后整个英国的兴起与衰落的过程。你通过一个个体看到一个复杂的时代,某种意义上,他的传记就是他的生活与他的时代。”
另一位强烈的影响者是传记作家罗伯特·A.卡洛,他用四十年时间写作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传记,不仅记述了这位总统的一生,同时也写出了他所代表的权力在美国的运转过程,包括整个美国社会的变迁。最令许知远感叹的是传记写作者为了理解那位来自德克萨斯州想要成为总统的年轻人,实现对他的生活想象,居然把家搬到了德州,并由此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孤独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青年时代的约翰逊。
不仅仅是传记写作者,再向前追溯,许知远提及大学时代读到的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书中不仅有麦克阿瑟、罗斯福、邱吉尔这些大人物,也能看到一个普通的退役老兵的生活,披头士的唱片怎么进入美国市场,甚至1953年美国安全套的销量,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改变……这种驳杂感令他兴奋。
在这些充满雄心的写作者那里,许知远意识到,我们对于近代历史人物的书写很少给予同样的时间与人的心理上的纵深,而令他着迷的正是这种通过一个个体看到整个时代风貌,以及由此构成的一个宇宙的多维感知。作为一个微电子专业出身的非学院派历史写作者,他反而有一种强烈的想要僭越的心情,盎然于传记写作带给他内心和现实的双重冒险。
“在写梁启超时,我也很想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广东年轻人突然被抛到日本的横滨是什么感觉,他周围的景观、人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去北京赶考,路过上海时,在四马路第一次买到那些翻译过来的书籍,感受到地球不只有中国,而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那个新鲜的世界是怎样的;他去美国访问,从西岸到东岸,都在卖‘李鸿章杂碎’,这种食物的配方是什么,…我希望能够写一部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同时这些细节又跟他个体的命运密切相关。”
在慌乱中拥抱世界的100年前的青年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许知远为什么选择了梁启超作为书写对象?这在传记首卷《青年变革者》的序言中已有所说明:“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大约十年前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许知远看见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裹头、皱眉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三人都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并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在第二卷《亡命》中,许知远给予梁启超更为具象的历史定位:“中国第一个现代心灵”。八月的分享会上,他对这一名词做出解释:他出生在1873年,正是帝国进入尾声的时期,他去世于1929年,正值北洋时代的终结。他的青年时代正是从19世纪向20世纪的过渡,他参与了时代的巨变。所以很少有人比他更容易折射这种转变。他所经历的转变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转变之初,某种意义上像是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对于日本社会的作用,他完成了一个新旧世界过渡中的桥梁的作用,这座桥梁所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和思想,更有对同代人丰富的勾勒。梁启超具有高度的丰富性。
一个广东新会的年轻人,20岁之前最远抵达的只有北京和上海,始于25岁的五年远行却是通往世界。他从天津登船出发,先到日本吴港,从那里再到达东京,开始在横滨的中华街落脚,创办《清议报》,又参与老师康有为创办的保皇会,到世界各地募捐,创建海外组织。他去过新加坡,穿越整个澳洲,回到日本,第二年又穿越整个北美,经过温哥华,到渥太华、蒙特利尔,再到纽约,最后以洛杉矶、旧金山收尾……这位经历了失败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旅行者,没有沉溺于挚友洒血、远离故土的创痛,而是深入各地散落的华人社区,面见各国政要,包括美国华尔街大亨,并与澳洲新兴华人精英产生关联,他在人生的慌乱、挣扎与不确定之中依然全身心拥抱了一个颠簸不停的新世界,以现代事业与现代思想,锻造出一颗属于现代世界的开放心灵。这种经验本身已足以给许知远写作的莫大鼓舞。
与主人公同步的沉浸视角
“历史真正的主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历史学家G.M.扬的这句话是许知远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也是他在写作第二卷时试图去寻找的一种感知。
许知远以看电竞比赛的经验来类比这种感知:“电竞比赛的现场观摩中有一个视角,与比赛选手同步,那是一个身处其中者不能够掌控周围所有动向的视角,正如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还原那种状态。”
不同于历史写作者通常采取的俯瞰式的上帝视角,许知远想要开启一种沉浸式的写作方式,历史人物不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过往或是博物馆中的陈列,他要带着这位历史主人公的视角,设想当时的他所看到的场景,感知的世界,以及身在其中的他的表现——他是一个25岁裹入巨大灾难、被推上亡命之旅的青年,他的朋友们在菜市口被斩首,他被抛入一个语言不通的新世界,他怎样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确认自己,同时又不被现实所摧毁,以一种新的能力来完成新的使命。“我希望自己在看待这些历史事物时不以‘后见之明’,而是站在与他同步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在行至美国纽约的章节里,许知远援引了《波士顿先驱报》的报道,它称梁启超为“东方的马克·安东尼”(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当日这张报纸活灵活现地报道了梁的一场演讲:“年轻的梁启超登上讲坛,慷慨激昂地指陈满清体制摇摇欲坠,沉疴难治”,四位助手帮助他展开一面旗帜,白底、镶红边、中间三颗星。他对台下说,第一颗星代表自我教化……第二颗星代表团结……最后一颗星是平等。他大胆告诉听众,他们与统治者是平等的,他们不需要向太后的官员磕头,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记者形容:“他指向旗子,就像马克·安东尼指向恺撒长袍上的裂缝。”
梁启超统计的纽约及附近布洛克岛上的华人数目也在书中呈现:他们中“洗衣者最多,杂碎馆者次之,厨工及西人家杂工又次之。”写到这里,当时流行于美国的中餐饮食中的“李鸿章杂碎”也浮出水面。在梁抵美的七年前,李鸿章访美,他的仪容、言谈与饮食趣味引发了当地人的好奇,于是便有了这道震动全美饮食界的“李鸿章的鸡肉大厨在华尔道夫所做的奇怪菜肴”。许知远甚至在书中附上了这道菜的菜谱。那一定也是令当时的梁启超好奇的所在。
而初抵纽约的梁启超也发现了美国人对中医的迷恋,中国药材在此皆以十倍以上的价格售卖。不过他对中国人的经商才能不无忧虑:中国的爆竹、葵扇、草席,每年输入本地后的销售达数百万美金,但这些生意主要由美国人垄断,中国商行寥寥……与此同时,他也不无意外地发现,自己也成了唐人街的景观,每当他在戏院演讲,街道即拥堵不堪,人们放下手中工作前来集会……
集成电路板式的万花筒叙事
驳杂的万花筒式的叙事大约正是这本传记不同于学院派历史专著的所在。书中,类似的细节不一而足。实际上有关梁五年流亡史的史料记述并不充沛。许知远在这一卷中使用的原始材料大多源自当时的英文报刊,而他也着实体会到了通过英文媒体探寻历史真相的乐趣。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他找到大量来自不同移民群体有关这位杰出的流亡者的报道,而对于梁启超这个名字的不同的拼写,在尝试与猜测之间,也让他颇费周折。令他印象深刻的报道中有一名留学生在西雅图聆听了梁启超的演讲,并对现场进行了详尽描述,他描写了当时一旁包厢里的一位着装西化的中国女士,而她就是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
许知远坦陈,卷帙浩繁的专业研究成果的确给予他的写作很多脉络线索,作为强有力的支撑点,但他所追寻的则是一个高度叙事性的历史写作,“它像是一幕幕电影,一章章小说的章节,从中看到人物的命运。就好像我在材料的重组中做了集成电路板,其中有思想的记录,有过程细节的记录,每个晶体管都有作用。”
自言拥有杂志式思维方式的许知远,以发散式思维重现梁眼中的世界:比如写到横滨,梁启超办报时的1899年的横滨是什么样貌?书中引用了凡尔纳在《环游世界八十天》中想象的横滨,还有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小泉八云对于横滨的描述共同呈现。再比如在澳洲,当地华人社区的样子,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什么……书中都有涉及。这些记述尽管琐碎,但当作者更充分地描述到梁所接触的世界的样貌,似乎他彼时的思想感受也变得更加鲜活了。
书中还有很多脚注,则更像是索引,它们说明书中信息的来源,比如一份波士顿的环球报的报道,有兴趣的读者即可找来阅读。许知远说,“每个索引都是一个通道,通向很多小的微观的世界。我期待这个书有很多窗口,甚至让你忘记梁启超这个人。”在写到梁启超在澳洲的交往时,书中就提到了一个当年的商人,澳大利亚的华侨实业家梅光达,他如何在一个新型社会里成长起来,成为当地一个华人社会精英,他与当时澳洲总督的关系,他的身份的模糊性——与清朝政府若即若离,对流亡者既有所期待又有些恐惧的心理……也都在传记中表达与呈现。或许这个万花筒式的非学院式写作方式,正是这本传记的吸引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