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年》 连 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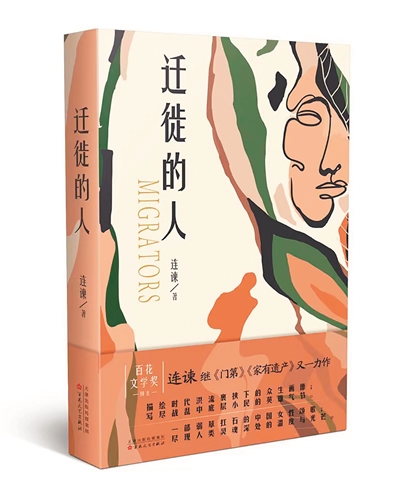
《迁徙的人》 连 谏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

《昨日之谜》 连 谏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我和故乡的每一个人,都是高密这片大地上灰飞烟灭的泥土,我们行色匆匆,低笑轻语,脚踏大地,眼望星辰,蝼蚁般下蛮力建设人生,就像不知道死亡终会将自己两手空空地带走。
——连谏
不写作时买菜做饭料理花草做家务,沉迷于朋友圈的话痨式自恋,写作时完全背对世界的喧嚣,将热气腾腾的尘世集于笔端。这是连谏,一位热切拥抱生活、致力于书写世情与故乡的女性写作者。
2023年,连谏有两本新书出版:《昨日之谜》,继续其驾轻就熟的都市情感写作,《流年》,是对记忆中乡土的一次深情探望,后者她更为看重。她说,随着年龄增长,心越来越开始向着故乡趋近,这促使她走出都市情感写作的舒适区。
在她看来,世间生命都是成精的泥土,有着各自的修炼阶层,或为植物,或为动物,以不同的生命形态在世间逍遥,死亡就是被打回原形,而她的父老乡亲就是成精的泥土的一部分,来这世上热闹。她书写这些形色各异的人们的情感,欲望、琐碎的生老病死,比之曾经的都市写作更显收敛与克制。
如同她的同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连谏的起风镇也风物渐长、人物日盛。从2022年面世的《迁徙的人》到这部《流年》,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努力抗争命运的摆布,却无力挣脱时代洪流的裹挟,他们庸碌、渺小、甚至卑下,但在连谏眼中,却有着美得像星辰一样闪耀的光芒。
如果说《迁徙的人》是连谏写作走上归乡路的起点,那么《流年》中的五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的故事,则让她回到故乡。她字斟句酌地拿捏乡音的秩序和节奏,并特别选择在平板电脑上写作,因为没有了键盘,书写的局限会让句式愈发简洁,最终跨度60年的故事只用了11万字。用最少的字写最跌宕传神的故事,这是连谏始终追寻的文字美德,她以此表达对文字的敬畏,以及对故乡书写的郑重。
从书写都市婚恋情感的圆熟到对刻在基因里的故乡的描摹的练达,在连谏的小说里,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人、对世界的宽宥与善意的态度,她笔下的人物即便背负了人世间再多苦难、沉重与不公,依然不会怨天尤人,依然会在遍尝悲苦后眷恋着命运曾经给予的糖。她以此种方式试图让这个尖锐锋利的世界变得圆融而温和。
对话连谏
关于写作的“五年计划”
“写城市是内心的恣意汪洋,写乡村是精神上的锦衣夜行”
青报读书:五年前一次采访中,您说会不自觉地给自己划分创作阶段,这样看来,从2022年《迁徙的人》面世,到2023年《流年》出版,是否可以看作是写作题材向故乡转移,由城市转向乡村的一个重要阶段?
连谏: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自己活不长,年轻的时候尤甚,所以,我从不设立什么终生梦想。人生计划,都是五年五年的来,总是胸无大志的样子,但也不觉得不好,这样,迫使我专注做好手头事,具有匠人精神。
搞文学艺术的,很鄙视匠人这俩字,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匠人意味着模仿,流俗,重复,没有创新精神和自己独特的风格,但用在训练对文字的驾驭上,我觉得匠人精神很好,现在的我不堪回首去看自己2005年以前的文字,觉得青涩矫情,在键盘上敲打了超过四个五年后,我已能接受自己现在的文字。
也是经历了这么多个五年之后,我才敢动手写故乡的一切人事与风物,对故乡写作的瑟缩不前,在我,就像离家多年的游子走在回乡路上,总有些近乡情怯,唯恐笔力不足,暗淡了故乡在记忆中的那一抹明媚而又温暖的亮黄。在我记忆里,故乡的颜色,是亮黄色的,像红彤彤的夕阳普照着成熟的谷子地,泛着橘色的光芒。
《迁徙的人》是2022年初出版的,但我是2019年开始写的它。从我的笔开始碰触到故乡到今年的《流年》,又一个五年已经快过去了,这是完全没计划的五年,跟着思维乱跑,我必须写下这些故事,它们是故乡的一部分,在我的身体里跌宕来去,犹如潮水荡漾,只有写完它,我的内心才能平静下来。
但这两本书的出版,不意味着我的创作将会由城市走向乡村,只能说,我终于敢碰触乡村题材了,把乡村也纳入我的可书写领域,让我的取材范围更广阔。写城市是我内心的恣意汪洋,写乡村是我精神上的锦衣夜行。
青报读书:莫言说,“每个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离开了这个地方,便离开了他生活的土壤,理解便无从谈起。”您是否更期待人们对于作家连谏的理解也从她生活的土壤谈起(类似莫言的东北乡),比如“起风镇”,而非一直以来大家心目中的情感写作天后?
连谏:我出生在高密,但对这个世界的审美,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建立,是在青岛完成的。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矛盾体,我生活在青岛这座沿海城市,内心里却时常觉得自己是个农民,走在街上,看到路边有一小块地荒着,我就会觉得可惜,恨不能去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粮食。
我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这样理解我:一个从高密来到青岛这座现代都市的乡下姑娘。
故乡高密和青岛这两个地方都给了我足够的能量加持,成就现在的自己。
经常看到媒体上称我为“情感天后”,对这个称谓,我很羞愧,也不知它是怎么来的,或许因为我之前给期刊写情感小说吧。所以,“情感天后”这个称呼,并不让我感觉骄傲,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画地为牢;相对而言,我对人性,对社会,对世间万物,更加好奇而好学,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我愿意穷尽一生做它的好学生,把我所学所得,用文字呈现出来。
写惊动了生命的记忆
“我的每一部作品,归根结底都是在试图穿越这虚拟的芸芸众生,探寻人性的光芒”
青报读书:无论是《迁徙的人》还是《流年》,都有从童年记忆中的所见所闻、耳濡目染中汲取素材和养分。好像许多作家都是如此,从自身经验和记忆出发来写作。记得福克纳曾说,我们童年的经验永远都不会耗尽。因为在不同的年龄回望过去,都会获得不同的认知和细节的发现。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当下的您,从那些过往的经验和记忆中收获的,和最想要表达传达的是什么?
连谏:这两部小说,都取材于我对故乡的零星记忆,或是即将在岁月的长河中随风而逝的一些零星记忆,它们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经年不散,说明它是以惊动的方式进入我生命的。
确实,如福克纳所说,在不同的年龄,回望这些记忆,给我们的触动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迁徙的人》中葛锦绣的原型,就是我爷爷的堂妹,后来回乡,都是站在村头看看就走了,因为我爷爷不许她进村,包括我爷爷去世,她回来奔丧,也是站在村口眼睁睁看着送葬队伍远去而不能加入……小时候心智未开,听了觉得解气,现在回头去看,觉得心酸,觉得可怜。这种可怜,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对众生,成长让我懂得了悲悯。
通过书写这些记忆,我理解了时代的力量,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人渺小又无助,不可能幸免于时代大潮流的裹挟,即便如此,好人依然是社会主流,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生力军,不管时代如何糟糕,人性的光芒部分都是人类这个群体的希望,哪怕只有豆丁大小,也能汇聚成耀眼光芒,也正是因此,我们才配得上这生而为人的生命旅程。我的每一部作品,不管是写乡村还是写都市,不管是写苦难还是写人生历劫,归根结底都是在试图穿越这虚拟的芸芸众生,探寻人性的光芒。
结局绝不会跑偏的创作
“我想要解读的生活本质比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更复杂,比如人性的幽暗与美好的并存”
青报读书:在读《昨日之谜》时,读者会想,如果洪雪娇没有在丈夫谢福哉面前信口胡诌孩子的身世,主人公“我”谢磅礴在童年时没有乱玩床头柜里的“白气球”,那把钥匙也没有被范小舟发现,每个人物的命运是否会不同;《流年》读到最后一篇《亲缘记》,也是一样,读者会想,如果李老汉没有去寻回女儿“福”,曲晓鸽也没有将那只玉手镯据为己有,故事的结局会改写吗?然而命运的齿轮一经转动,便已注定。作家在写作之初是否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戏剧性的构架?
连谏:我的小说,在写之前,框架都是已经搭好了的,甚至有些细节,也都已丰满而成熟地贮藏在我心里,在我内心深处生长了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长成了一棵丰茂的大树,开始创作,就是坐在电脑前,把它输出就行了,但在输出过程中,思维也是千变万化的,也会跑偏,但结尾不会跑偏,因为故事的结尾就是我输出观点的终点,它是万不可以跑偏的。
小说中我也说过这句话:人生没有如果。这句话,对我,太警醒了,说残酷一点就是人生没有回头路,这迫使我必须认真面对我的生活,半点马虎都不能有,因为人生没有如果。
这两个故事的架构,也是在人生没有如果的基础上,但所有人的人生,都是由无数个不能回头的如果组成的。我们现在过着的人生,不过是从无数个如果中选择其中一个如果而已,没有成为悲剧,是我们在选择这个如果的时候比较慎重,回避了它可能出现的悲剧性如果。
青报读书:不论是书写现实抑或过往,您的每一部小说的叙事似乎都带有类似的宿命感,这是您想要揭示的生活的本质吗?
连谏:是的,但我想要解读的生活本质比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更要复杂,比如人性的幽暗与美好的并存,它的复杂,是多少文字都无法阐述清楚的。有句话说,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雷姆特,那么千万个作家书写生活,就有千万种生活的样貌呈现,每一种生活的样子,都是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表达。
青报读书:有人说作家都是雌雄同体(《昨日之谜》就使用了男性第一人称的视角),您认同这种说法吗?都说文学是用来共情的,女性是不是更容易与读者形成共情?
连谏:男人和女人,除了生理结构不同,人性都是相通的,我认同作家都是雌雄同体这个说法。但在男女情色方面,不管是男人写女人,还是女人写男人,都隔着一层朦胧薄纸,因为女人无法透彻地体验男性,男性也无法体验女性,不能体验的人生,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代入女性内心世界更容易一些,也会成为下意识,所以,我写女性比写男性更鲜活生动。
在我的理解中,阅读文学作品,和看电视看电影一样,是一种爱好性质的消闲,在消闲同时获得精神愉悦,或者说得到精神抚慰,这种抚慰,就是共情。作品与读者之间达成共情的能量越强,作者的书写功力越深,女作家并没有抵达这种功力的捷径。能否与读者达成共情,是作家必须抵达的及格线。
选择宽宥的主人公们
“对人、对世界多一些慈悲的包容,会让这个锋利的世界圆融而温和”
青报读书:有一点必须提及,是您小说中几乎未曾显现和描述过的一种情绪:极端的怨怼和仇恨。《昨日之谜》中,即便遭遇了诸多不幸,最终也只有男主人公的自省和谢罪,小说自始至终都在貌似轻简跳脱的语言叙事中讲述;《流年》更是如此,面对命运弄人,人生苦难,年轻时的李老汉感叹人世间真好;年老时的李老汉开导为他鸣不平的人:欠下的总是要还的,舒心地闭眼;轮到孙辈的李第一,也选择了宽宥,说:宽宥自己,是尝过再多苦也眷恋着这个世界曾给过的糖……还有那个很特别的比喻:“人生像巨大的创可贴,一层又一层地糊在他心上,是沉甸甸的、伤痕累累的愉快。”想知道,是因为不能承受生命之“重”,所以才刻意在写作中诉之以“轻”吗?
连谏: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都从不书写极端的怨怼和仇恨。因为我不喜欢仇恨。
很多年前,我就不喜欢阅读关于复仇的文学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我对所有复仇的文艺作品都很排斥。仇恨是一剂毒药,对自己的伤害,远远大于要被报仇的那个人,所以,尽管小说作品要有爱恨情仇才能形成故事的路线,作品中的人物会在爱恨情仇中挣扎煎熬,但我最终都会让我的主人公们选择宽宥。
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仇恨,就像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武器。所有输出仇恨的文艺作品都是精神毒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苦的,穷人以为有钱了就会幸福快乐,却不知道有钱人的痛苦沉重,因为钱都无解的痛苦,才是真的痛苦。
希望阅读我作品的人,学会换位思考,没有换位思考的人生,是动物性的人生;学会自省,不自省的人生,是远离成长、远离神性的人生。对人、对世界多一些慈悲的包容,会让这个锋利的世界圆融而温和。
《昨日之谜》的行文虽然诙谐俏皮,但《昨日之谜》是忧伤的,我经常写着写着就难过起来。我不喜欢用愁云惨雾式的文字书写忧伤,这样会陷入刻意卖惨的煽情,相反,我希望我塑造的人物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把自己赤裸裸地坦诚在读者面前,而不是一个被矫饰的情绪装饰在读者面前的角色。真诚永远是打动读者的不二法宝。
不管是《昨日之谜》中的谢磅礴还是《流年》中的李第一,他们背负的生活都太沉重了,写作的时候,我必须让他们轻起来,否则读者会被沉重压得透不过气的,以轻言重,就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轻”,这种必然会坠落成齑粉的轻,令我黯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