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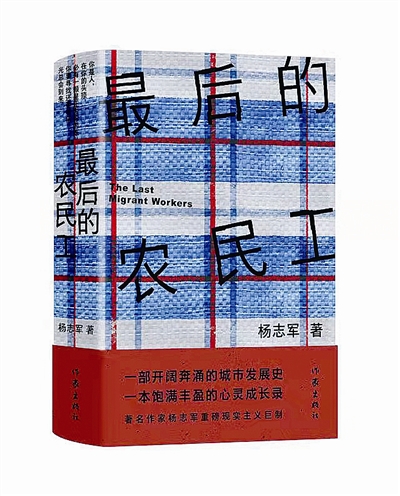

余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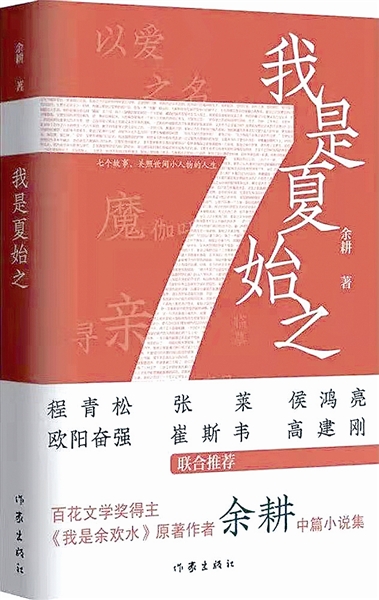

连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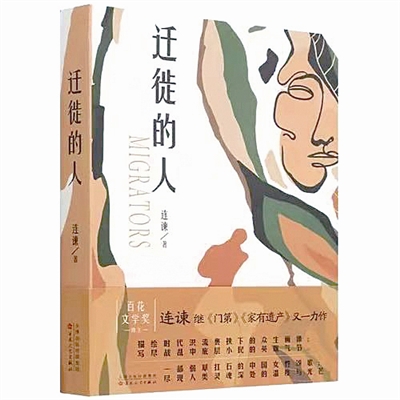

阿占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显然,作家拥有此种能力。年末,我们以通俗而直给的设问,记录四位青岛小说写作者的生活与思考。他们都是2021年度青岛小说界的醒目存在,或有新作问世,或有奖项加身,而对写作者自身而言,精神层面的全新觉知与突破才更值得说道。
这份青岛作家的年度记录将为2021年留下文学的鲜活注脚,写作者将他们审视生活的日常视角传达给我们,不仅仅通过作品,更有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与体验。作家福楼拜说,“文学就像是炉火,我们从他人那里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以致为大家所共有。”这是文学的使命,亦是作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杨志军:阅读是呼吸,写作是深呼吸
2021年,作家杨志军的新长篇《最后的农民工》面世,并位列作家出版社年度20种好书之一。
记者:这一年写作有哪些进展和突破?
杨志军:我的写作一如既往地关系到都市海洋和青藏高原两方面的生活,它让我的思考与体验变得开阔而多变。一直都想沉下来,表现那些最应该表现的人与物,对青岛的抒发拉近了我跟社会的关系,对青藏高原的描写又让我持续保留形而上的思考。“人”的质量、“人”的模样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是我一真没有放弃的两大主题,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和此前出版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恰好对应了我最初的作品《大湖断裂》和《环湖崩溃》所关注、忧患的问题。可以说突破的只是题材,而思想却一如往常地执拗着。文学表现的是经过思考的生活,无论你写什么,其实都是写自己。
记者: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有出现那种文思如泉的“心流”状态吗?发呆和动笔的时间各占多少?
杨志军:就像必须完成命运布置下来的作业,总有写不完的东西纠缠着我,享受发呆的机会很少,但并不表示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有效的动笔时间平均每天也就五六个小时。“心流”是有的,但来潮的似乎并不是文思,而是一些奇情异想,比如单数的对称性、社会的物理学特征等等。
记者:关注思考的领域或是热点话题是什么?
杨志军:所有的热点话题都不关注,因为需要冷静思考,冷静意味着距离,远一点看似乎更清楚,所有的热点都是大笔触快笔锋的油画,离得越近越模糊。一个人要善于走出来,而不是凑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关注的都是历史。
记者:一年中您读了哪些书?近期更偏爱哪一位作家?阅读对您而言是怎样的存在?
杨志军:我读历史多一点,也比较杂。阅读是呼吸,而写作是深呼吸。
记者:这一年去到这座城市的哪些地方,有哪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志军:……不好说。
记者:在您看来,当下作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杨志军:文学、音乐、绘画这是人类的三个精神维度,缺少任何一个,人的精神就都是扁平的,而不是立体的。无论什么时候人都不会枯竭精神需求的欲望,所以越是沉陷在精神寻梦中的作家就越有价值。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包括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寻找并实现作为人的可能性,作家是通过书写,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价值就越大,也就是说作家的价值在于寻求人的可能性的广度和深度,在于思想的质量和能量,而不在于技巧。
记者:新的一年有怎样的人生计划或是写作计划?
杨志军:没有什么计划,活着,呼吸和深呼吸。
余耕:遇到热点,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2021年,余耕的中篇小说集《我是夏始之》获得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位列作家出版社年度20种好书,并获评“最具影视改编价值图书”。
记者:这一年写作有哪些进展和突破?
余耕:这一年的写作没有任何进展和突破,我上半年写完两个中篇小说后,一直处于休整阶段,原因是我已经连续写了十多年,几乎连春节都没有休息过,有一年大年三十还在写作。一个小说写完后,几乎没有超过一周,便开始了新作品的创作。今年下半年,我几乎一直都在读书和旅行,或者是参加新书的读书会。我觉得我需要一段这样的休闲时光,虽然我时常会产生负疚感,觉得辜负了半年时光。但是张弛有道,磨刀不误砍柴工。
记者: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有出现那种文思如泉的“心流”状态吗?发呆和动笔的时间各占多少?
余耕:我的写作状态一直比较平稳,几乎没有太大的起伏。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像上班族一样,洗漱、早餐、喝一杯咖啡后就开始坐到电脑前面工作。当然会有“文思泉涌”的时刻,每当此时我也会倍加珍惜。当然,也会更加谨慎地审视自己的“泉涌”是精华还是垃圾。这样的鉴别,通常发生在第二天写作之前,我会把前一天写的内容审读并加以修改,当然也可能全部删除。创作过程中,发呆和动笔的比例大概是7:3,七分发呆,三分动笔。
记者:关注思考的领域或是热点话题是什么?
余耕:我关注的领域比较多,几乎是社会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教育、民生、影视、娱乐、体育、哲学、可学、玄学……但是我有能力思考的领域没有这么多,一直以来几乎都是一边关注一边学习。当然,也会关注热点话题,俗称“吃瓜”。但我很少参与其中,因为生活远比戏剧精彩,很多热点都会有戏剧性的翻转。遇到热点,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记者:读了哪些书?近期更偏爱哪一位作家?阅读对您而言是怎样的存在?
余耕:我读的书比较杂,尤其是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五花八门的相关书籍都会扫一眼。近期,比较喜欢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和安吉拉·卡特,还有王鼎钧。阅读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一条高速公路,只要有足够体力,我便可以通过阅读走向远方。
记者:这一年去到这座城市的哪些地方,有哪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余耕:相对于这座城市的海,我更喜欢这座城市的山。我今年去了北九水和华严寺,很惭愧,作为一个崂山人,我居然是第一次去这两处地方。今年秋天一场大雨过后,我去了北九水,山泉奔涌,一泻而下,人在山水间,有种融入自然的心境。同时,我也惊诧,崂山里面有这么秀美的山水,我却忽略了它们半个世纪。华严寺也很棒,我觉得是崂山最有气场的宝地。为了这两处地方,我特意办了一张进山卡。
记者:新的一年有怎样的人生计划或是写作计划?
余耕:近两年的人生计划都要视疫情而定,与北京、成都和云南的朋友都约了很久,新的一年里希望能够相见。关于写作计划,我想写一个历史小说系列,已经有了初步规划,会在年底开始动笔。另外,也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天下太平。
连谏:文字的世界,让我永远心怀感激
2021年,连谏的首部年代小说《迁徙的人》出版,短短几日,这部“大女主”的家国大戏就跻身“当当”当代小说销售排名前十阵列。
记者:这一年写作有哪些进展和突破?
连谏:这一年,在创作修改一个剧本,也开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卖出了院线电影版权。这一年,自己最大的突破,就是在写作上变得佛系,如果我没深思熟虑,不再会像过去一样逼自己去完成它。这个变化应该是年龄的馈赠,我挺喜欢的,无论在写作态度还是在写作表达上,我想更“自己”一些。
记者: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有出现那种文思如泉的“心流”状态吗?发呆和动笔的时间各占多少?
连谏:写作状态很端正,想写的时候,排除一切干扰,坐在电脑前,心无旁骛。文思如泉涌的心流状态还是经常有的,比如我在写中篇小说《祝你幸福》的时候,写着写着,有种要起飞的感觉,这对于写作者而言,是最幸福的状态。
发呆的时间很多,如果把一年平均分成十份,我大约有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发呆中度过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奋笔疾书的。其实,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发呆就是在发酵,相当于砍柴人在磨刀。
记者:关注思考的领域或是热点话题是什么?
连谏:我现在非常关注当下的社会形态,关注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在往哪个方向走。年轻人所形成的当下社会形态,就是时代的热点话题,我很想了解他们,因为他们即这个世界,即未来。
记者:读了哪些书?近期更偏爱哪一位作家?阅读对您而言是怎样的存在?
连谏:今年我杂七杂八地读书,完全不系统,都是抓过哪本来读哪本,最近放在床头的是李修文的《山河故人》。
我一直以来偏爱的作家都没改变过:老舍、莫言、加西亚·马尔克斯、余华……还有很多。
近两年,我从以前热爱读小说转向了阅读人文类书籍。对我而言,阅读就是聆听高人一席谈,是我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阅读,我的内心世界可以去往很多遥远的、我的肉身可能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所以,对文字的世界,我的内心是充满感激的。
记者:这一年去到这座城市的哪些地方,有哪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连谏:我去了郊区的青山村,在崂山山脉的深处,僻静,悠远,是城市生活的另一种样子。很感慨,其实,青岛这座城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还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想到这里,就会想起诗和远方,连身边的好景色都没看遍,谈何远方呢?人类其实是很矫情的,这种矫情,是自我存在感的强调。
记者:新的一年有怎样的人生计划或是写作计划?
连谏:新的一年,计划写一部倔强的小说,所谓倔强,就是不搭理这个世界,埋头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桀骜不驯地写完。还想写一个超级牛的中篇……希望我能如愿完成它们。
阿占:诸神在黑夜里留下黑金,只有早起的人才能捡到
2021年,称得上是阿占(王占筠)的丰收之年。短篇小说《制琴记》获得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制琴记》和散文集《海货》,即将在2022年春节前同时出版;中篇小说《墨池记》首发并被多家知名期刊转载,亦是好评如潮:“全篇写的是学书,讲的却是情感。法的传承,既是书法技艺上的,更是精神情怀上的,潺潺流在笔墨之间,疏通了人的经络,直让五脏六腑充溢着暖流。”
记者:这一年写作有哪些进展和突破?
阿占:今年如去年一样,甚至如过去的二十年一样,写作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所谓的“进展”就是持之以恒,所谓的“突破”就是澄思寂虑。
记者: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有出现那种文思如泉的“心流”状态吗?发呆和动笔的时间各占多少?
阿占:我每天5:30左右起床,从1997年开始写作算起,可以说这个规律从未被打破。诸神在黑夜里留下了黑金,只有早起的人才能捡到。清早给予我清冽之感,故而思路敏捷,我很喜欢把天写亮的感觉。天亮后便出门锻炼40分钟,根据季节的适应性,我选择游泳或慢跑。运动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运动结束以后,当天的“任务”就基本捋明白了。
所谓“心流”就是“神来之笔”吧,有时候,我会获得这种奖赏,这种奖赏能助力我打通天地人间万物诸事,走出迷途。更多的时候,我在迷途中看见了自己的疲惫。眼睛变得锈而钝,吱吱剌剌。一天漫长,一小时漫长,一分钟也漫长。如何找到那个逻辑缜密、派词恰当、见血封喉的节点?这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
记者:关注思考的领域或是热点话题是什么?
阿占:我关注“泛艺术”领域。一方面对于当代艺术展、独立音乐节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诸如书法、戏曲、武术、中医情有独钟。建筑、园艺、电影、室内和服装设计也同样让我着迷。如果从写作的角度来讲,我关注海洋文化与生态、关注城市进程中的老城区命运、关注天下匠人,也关注头生反骨的人。
记者:读了哪些书?近期更偏爱哪一位作家?阅读对您而言是怎样的存在?
阿占:今年的阅读可以说相当“功利”,闲书读得少,多是为写作需求而读。比如苏沧桑的散文集《纸上》,书中收入《春蚕记》《纸上》《跟着戏班去流浪》《与茶》《牧蜂图》《冬酿》《船娘》7个中篇散文,剪裁了一出出浓郁的江南世俗生活。《纸上》构思可见精妙,作者混同小说的艺术手法,结构上使用并置叙事。又因作者致力于田野调查,对现场的介入力度更大、程度更深、时间更久,这也是我所共鸣的地方。
还读了余华的《文城》。余华似乎在以一种寻找的方式抵达精神上的乌托邦。旧书新读,主要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代表作,和二十年前的顿挫感不同,今年我把历史、现实、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拆除,找到了一条穿梭往来的通道。《青岛围城日记》亦是重读。作为日德战争丛书,文章取自战争亲历者的第一手记录,对于我进一步了解老城的沧桑构成很有帮助。
记者:这一年去到这座城市的哪些地方,有哪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占:我经常进行田野调查,今年一如既往地跑渔村、离岛,所剩不多的古老渔村里,都有我的渔民朋友。我也经常在老城里来回走,拜访老人与老房子……我喜欢沉潜下去,直到把某些地方变成心里的地方。因为疫情原因,也只能这样了。
记者:新的一年有怎样的人生计划或是写作计划?
阿占:2022年准备出版一部中篇小说集,目前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同时长篇小说《潮汐》也正在逐步推进,这部小说被列入“山东省优秀文艺作品孵化项目”和“文艺精品创作质量提升工程”,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并探究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书写百余年来胶州湾的精神图谱和半岛地区的旧邦新命。
